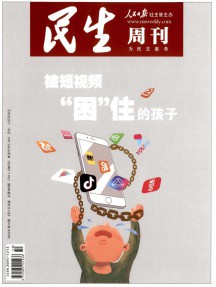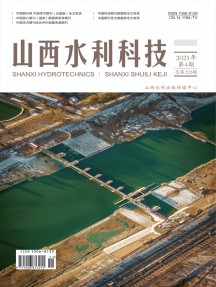生態美學的美學觀念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9 17:40:30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生態美學的美學觀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生態理念設計已經逐漸成為校園景觀設計的宗旨,目的是為了創造可持續的校園景觀。闡述了校園生態設計理論與應用的現狀,對校園生態設計原則與思想以及校園生態景觀設計系統進行分析研究。
關鍵詞:
生態美學;生態設計;校園景觀;可持續設計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環境的要求日益提高,改善高等教育環境迫在眉睫。大學校園越來越人性化,大面積的綠化改善了校園環境,提高了學校形象。在進行校園綠化的過程中,應該認識到這不只是簡單的綠化,還應該考慮到校園景觀中豐富的生態性。
1生態美學
所謂生態美學,是生態學和美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生態美學是研究人與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具體的研究對象是對人類自身生存狀態的生態思考和對人類生存環境美學關系的研究與思考。
2我國生態美學理念下的校園景觀設計現狀
景觀設計學科本身在我國的發展時間不長,在設計過程中很少有考慮到生態美學方面的內容,所以,從生態美學理念方面來考慮,校園景觀設計還處于盲區。現階段的大學校園景觀設計多停留在設計本身,也就是其形式、紋理、樣式等,少數考慮到人在其中使用的,也都是淺顯的并未深入到生態美學的層次。因為在景觀設計的過程中,我們不只要考慮物質文化的需要,也要考慮到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就是生態美學在校園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上的應用。
2.1生態美學在大學校園物質文化建設中的應用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是生態美學中最首要的關系。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可以說是校園物質環境按照人的意愿進行改造,人是校園環境的影響者,人可以按照主觀意識來改造校園。馬克思曾說過:“人類可以創造環境,同時環境也可以創造人”。環境對其中的審美者進行影響,審美者自身的心理及行為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產生或多或少的變化。校園的物質文化建設從生態美學角度上來看,主要體現在校園自然文化(包括人文景觀、自然景觀)方面。西方早期的大學多選址在鄉村或者城郊地區,厚重肅穆的建筑和優美的鄉村景色,給人以心靈的凈化和寬慰。大學校園應該給學生營造一個安靜的氣氛,通過建筑與景觀以及整體建筑風格和整體景觀風格都應該統一,相互融合,也要結合校園周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校園自然景觀建設包括校園原始保留的自然風景、校園內的花壇草坪、景觀雕塑等,自然景觀是最貼近學生日常學習生活的物質環境,以客觀的存在展現美,具體可分為自然美和形式美,自然美是校園環境的基礎,樹木、石頭、花草皆是自然美的表現,有些大學還保留著整體性景觀的自然美。人文景觀根據特定歷史或人物背景,或者特定場景環境產生的景觀,一般具有教育意義,如雕塑等。人文景觀對于個體情感的思想展現具有很大作用,校園內的人文景觀在結合了歷史文化名人之后,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蘊。
2.2生態美學在大學校園精神文化建設中的應用研究校園精神文化的建設也離不開生態美學理論,校園的精神文化建設,其實就是人與人自身的關系建設,用生態美學的方法處理人與人自身的關系,才可以為大學校園的全面發展提供幫助。在生態美學中,有一個原則就是人和其自身的發展進步原則,這個原則的目的是為了人本身,作為生態中的一部分,研究人自身也是有意義的,為了人本身的發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態美學關系。大學校園中,老師和學生是創造校園的中堅力量,老師和學生和睦相處也是校園生態建設的重要保障之一。
3生態美學在大學校園景觀建設中的應用
生態美學在人與自然和人與自身方面,對校園景觀建設都有指導作用,人與人自身方面則更偏重于哲學問題。在校園生態景觀建設中,人與人自身關系的問題起到了引導作用,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主要考慮的還是人與環境、人與氣候文化以及經濟、人與生態的關系問題,校園景觀的生態設計是基于如果校園內環境條件允許,可以利用自然力但不進行大規模破壞,嘗試風能、水能、太陽能來發電。校園景觀設計中的人文景觀、可持續生態景觀等都會對學生產生教育意義,讓學生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諧,珍惜校園環境。除了以下這些總體的概念,還應考慮一些細節,比如,設計取材應多用當地石材和植物,減少資源消耗,節約能源,大面積鋪裝選擇本地石材,少數非本地石材在選擇過程中也要考慮到衛生及安全問題。
生態美學理念中,不僅包含人與自然和人與人自身的發展問題,同時還包括自然與自然自身的發展問題,自然本身也具有能動性,當它遭受破壞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進行自我修復、自我調節和發展。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變越大,自然環境的這種自我調節能力就越弱,所以,在設計校園景觀過程中,應當盡量多保留現有的完整生態環境,才能使環境的自我發展得以實現,為廣大師生帶來一個和諧、美好、充滿生機的大學校園。
參考文獻
1余樹勛.園林美與園林藝術[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
篇2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基本精髓與傳統哲學基本命題中,“天人合一”思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美學的主要探索問題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首要的研究內容。中西方的美學觀念中對生態思維、生態意識、自然觀等方面存在的分歧較大。在西方美學觀念中,對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過于頑固,提倡人類征服自然的觀念,在中國的傳統美學觀念中則認為人與自然及其他存在物應和諧共存,對生物圈中甚至是全宇宙中的所有事物應共同繁榮和生存。自20世紀末開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產生了矛盾,并日益的形成對立關系,使生態問題逐步的凸顯出來,此時美學家和哲學家則開始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行反思,西方
美學的發展也因此受到了阻礙,但是中國的“天人合一”觀念則將其強大的生命力顯示出來。本文對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對西方美學走出困境的啟示進行了探討。
一、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美學觀念
自然是中國傳統美學的主要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最基本的精髓,對“人”和“天”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人類來源于自然;人類應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自然規律和道德原則是相同的;人和天應協調和諧共存。“天人合一”的思想存在于中國的道家、儒家、佛家思想中,是較為宏觀的人和宇宙萬物關系的理念,和諧則是人與自然的共同含義。
按照不同的理論可以將美學分為智慧美學、知識美學、趣味美學。智慧美學是人類超越了知識的范圍,提高到審美智慧的方面。知識美學則是對審美規律的概念范疇和知識譜系進行重視。趣味美學則是對人的感性審美趣味和經驗進行重視。智慧高于知識,莊子的思想認為最高層次的智慧應該是將自我和天地萬物進行遺忘,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自身,曠然無累,自我和天地萬物和諧統一。所以當自我和人、自然和社會做到了和諧,則宇宙萬物和人類生命之間將不存在界限。
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念是一種生命美學的體現,將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和極大熱情進行了凸顯。認為宇宙間的一切事物應做到和諧,對和諧的生命精神進行了提倡,并對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人和自我的相交和諧、共同創化進行了重視。
二、 西方美學的困境分析
在西方美學觀念中缺乏對宇宙萬物生命的思想,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這種所缺乏的思想卻被宗教所利用,認為上帝創造了一切,從而對萬能的上帝進行崇拜和贊美。
在西方美學的觀念中沒有對事物進行結合思考,只是一味的在所謂的科學體系中和學科門類中存在自身的立足點,認為只需要一看分門別類的分析和研究便可以促進學科性、科學性美學的形成。
對立的二元論是西方美學的思維方式,通常將事物一分為二來進行思考,使兩方面處于對立位置。并且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是無法進行協調的,人類必須對自然進行征服才可以使自身的價值得以實現,人類也必須遵循弱肉強食的生存理念才能和自然的發展規律相符合,這樣的思想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使自然成為了人們掠奪、奴役、支配的對象,也使得人與人之間也存在著無端戰爭和激烈競爭的現象。
總而言之,二元論思維和理性分析備受西方美學的推崇,將構建相應的知識譜系作為理論研究的根本目標,并且想以此作為西方美學能夠走出困境的新方法。但是西方文化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時代開始,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轉載須注名來源便對人類的科學意識進行了自覺性的培養,對人的理性分析精神進行了極度發揚,并將世界劃分為分門別類的學科開展探索研究,曾一度獲得了豐厚的成果。從此,人類辯證征服自然的過程中逐漸的自我膨脹,促使了人類是宇宙萬物主宰這一思想觀念的形成,形成了以人類為中心的觀念,西方美學則始終被這一思想所困,無法得到長遠的發展。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雖然進行了大量物質財富的創造,但是卻無法對安康、幸福的生存進行享受,反而因為嚴重的破壞了生態系統,使環境惡化,對人類的生存和精神方面產生了危害,引起了西方美學家的反思。
三、 中國“天人合一”觀念對西方美學的啟示
由于西方美學中存在的漠視生命、背離自然思想,使西方美學的發展受到了阻礙,為了能擺脫這一困境,西方美學可以從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中借鑒一下幾點策略:
西方美學應摒除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要樹立以生態為中心的觀念。由于西方美學中,以人類為中心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則在《政治學》中提出“植物的存在是為了給動物提供食物。所以,所有的動物都是大阻燃為了人類生存而創造出來的。”等觀念,這些觀念的存在為人類征服自然、統治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力量和理由,使西方人類和環境、文明、自然之間的惡化關系愈演愈烈。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中以生態為中心的思想形成的較早,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生存。老子的思想中認為人來源于自然,與蒼宇相比,人就如高山中的一株樹、一棵草而已。老莊思想也認為人要回到人類本身之中,要慎重的對到生存和存在,防止人類出現自我膨脹的觀念,對人們追求和諧生存的觀念進行了引導。以生態為中心的科學性觀念通過生態學的豐富和發展得到了體現,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則是古典的生態美學中的一種,凝練了古代生態美學的思想觀念。所以西方美學應從中國“天人合一”美學觀念中進行養分的汲取,是走出困境的明智選擇。
西方美學中的二元論思想使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對立,并將自然視為人類征服和統治的事物。中國的“天人合一”美學觀念中則是對和諧生命精神進行提倡,對人和自然之間的相交和諧關系進行重視,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觀,生命和宇宙的和諧觀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美學觀應對知識譜系的建構進行轉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存在進行接受,做到對自由創化的生命智慧和生命精神予以尊重和體悟。改變對美學的不正確看法,應將美學視為一種對人與自然之間、生命之間和諧共存的思想和智慧。
篇3
一
研究生態美學,首先應該回答“什么叫生態美學?”這個問題也是確定生態美學的研究對象。王著對此有著明確的說明:“生態美學的任務可以被界定為,使用現象描述和本質直觀的方法,研究現實世界以及文學作品描繪的日常生活世界場景中人與自然交往的關系,通過這種研究擴展對自然事物的理解,在主體性存在的框架中發現自然事物在物質性之外所具有的存在內涵。”①這里盡管是在說明“生態美學的任務”,但其實是在界定生態美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就研究方法而言,王著明確提出是“現象描述和本質直觀的方法”――這正是現象學的基本方法;就研究對象而言,王著明確將之界定為“現實世界以及文學作品描繪的日常生活世界場景中人與自然交往的關系”。王著在另一處更加簡明地指出:“現象描述和本質直觀是現象學的基本方法,它幫助生態美學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即通過研究現實或者文學所展現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與自然的交往方式闡釋自然超越物質存在的豐富內涵。”①正因為作者采用的是現象學的方法,所以她將自己的生態美學稱為“現象學生態美學”,從而區別于國內外已有的生態美學立場。
那么,如何看待這種生態美學觀呢?上面引用的兩處界定清楚地表明,作者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界定生態美學的研究對象的――這個研究對象說到底就是“自然”,也就是對于自然的審美欣賞與審美表達,用王著第四章第二節的標題“從現象學的自然美學通往倫理學”來概括就是,作者所研究的其實是“現象學的自然美學”。如果這個概括符合王著原意的話,那么,王著必然面對一個學術質疑:“生態美學”與“自然美學”是否能夠等同?如果不能,那么二者的區別何在?
眾所周知,所謂“自然美學”就是以自然作為研究對象的美學,它將研究對象限定在“自然”上,從而將人類文化創造的產品(包括一般的審美文化產品和藝術品)排除在外。“自然”作為審美對象普遍地出現在古今中外的審美活動當中,因此,關于自然的美學理論層出不窮,比如,中國古代有著豐富的自然審美理論,當代西方環境美學當中也有極其豐富的自然美學理論。作者對此當然有著清醒的意識。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自然”,而這個問題又包含兩方面的思考:一是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看待自然?二是進入人類審美活動中的自然到底是什么,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事物、康德意義上的自然本身,還是其他什么?王著正是通過論證這兩個問題而把自己的“現象學生態美學”區別于一般的“自然美學”。
就這里思考的第一個方面而言,王著提出,我們應該帶著“敬畏之心”來看待自然。王著非常精彩地論述了“敬畏之心來自哪里?”這個問題:“敬畏的來源也許有很多,當最偉大的科學家們發現自然的奧妙永遠不是人類的理論所窮盡時會有敬畏之心,當普通人遭遇到人力所不能及之自然奇跡時會有敬畏之心,現象學提供給我們的則是理性在自我質疑、自我辯駁和突圍中終于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時產生的敬畏之心……現象學的敬畏是在經過艱苦的理性思辨之后,由理性自我逼問而達到的極境。正因為這個自我逼問的過程縝密而充滿理性,其逼問的結果才能具有強大的說服力,理性對于自身有限性有了足夠清明的認知之后才能為敬畏之心的建立打掃出一片空地。”②眾所周知,敬畏自然是當代生態倫理的核心內容之一。心存敬畏之心去欣賞自然不同于一般意義的自然審美,尤其完全不同于房地產開發廣告中所隱含的“自然美”的觀念,它可以被叫作“生態的自然審美”。盡管王著并沒有明確地采用這樣的表述方法,但是,它對于敬畏之心的論述表明,它也比較清醒地將生態倫理視為自然審美的前提。
就上面提及的第二個問題而言,王著別出心裁地提出了“如自然”概念,用來區別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事物以及康德意義上的自然本身。王著提出,所謂“如自然”就是“好像自然那樣的意思”,“如”借用了佛家用語“自然真如”消解自然實體性意味的內涵,它的提出恰恰是為了批評常見的“真實的自然”這一概念。王著認為,生態批評的直接價值不在于陳述任何一種保護自然的實踐行動或者直接指向現實行動的指導觀念,而是通過恰當分析作品中的“如自然”,精確恰當地陳述其中所隱含的自然理想、自然觀念,幫助我們理解的不是所謂的自然本身,而是“我們自己如何理解自然”①。
王著對于“自然”的上述兩方面論述,有助于其“現象學的自然美學”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美學”而走向“生態美學”。但是,筆者還是對此保持不同看法。筆者一直堅持從審美方式而不是從審美對象的角度界定生態美學,一直認為生態美學的研究對象是“生態審美”,也就是借助生態知識、立足生態倫理意識的審美活動②。“生態審美”的對象既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包括生態文學在內的文藝作品、審美文化產品等。也就是說,筆者一直重視生態學和生態哲學在構建生態美學中的重要作用。這樣的思路與王著有著明顯的差別,王著明確提出它“堅持的一個基本信念是”,嘗試從人文學科自身獨特的思考脈絡和思考層面上理解“生態”問題,“而不是將生態科學或者生態哲學方法直接拿來套用到美學和文學研究中”。王著對這些方法一直保持反思和批判的態度,“因為它們無論在理解自然事物還是人類自身時都沒有從根本上擺脫二元論的對象性思維方式”。王著認為,它以現象學為基礎的生態美學研究堅持徹底的“主體性”一元論立場,認為自然事物以及生態問題只能從“人的存在”這個絕對基礎出發才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③。筆者認為,王著這里表達的學術信念和學術立場值得認真討論,這個討論可以概括為如下兩個學術問題:其一,在構建生態美學的過程中,應該怎樣看待生態學和生態哲學?其二,現象學與“主體性”一元論之間是否有著必然聯系?
二
由于王著將自己的研究主題確定為“現象學的自然美學”,它為自己設定的核心問題都與自然有關。比如:自然事物的主體性應當如何理解,它與人類的主體性是同樣的意義嗎?生態整體的價值何以判定,是誰來判定的,人類自身的文化觀念、思想意識是否包含在生態整體的范疇之內?現代人對生命、對自然的“敬畏”之感從何而來,“自然”如何能夠重獲現代人的尊重?在自然中的審美經驗有什么現實意義?王著致力于對這些對問題的進行深入反思,從而確定生態美學(以及生態批評)的身份。帶著這樣的寫作動機,該著試圖借助現象學方法為上述問題尋找答案,從而形成了全書結構的隱含脈絡。王著進而認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正是生態美學理論的組成部分,其回答方式是具體研究代表性的現象學家,試圖通過對諸位現象學理論的細致解讀,來逐步展示生態美學理論的完整面目。從這種思路出發,王著將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杜夫海納以及英伽登等五位現象學家及其理論放置在生態美學(或生態批評)的問題視閾中,“在生態文化的問題視域中與現象學理論進行對話,構成生態美學理論的是這種對話的結果,而不直接是某個現象學家的理論”④。正因為這樣,王著才將自己所構建的生態美學稱為“現象學生態美學”。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要采用現象學方法來構建生態美學呢?或者說,現象學理論可以為生態美學提供哪些借鑒呢?王著提出了如下四點:首先,現象學反對現代科學與哲學方法中事實與價值、主體與客體、人和世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這與生態美學對生態危機思想根源的批判完全一致,正是在對現代自然科學二元論思維方式的批判過程中,生態美學和先驗現象學獲得了接近的可能性。第二,現象學凸顯了研究的主體化視角,研究在人的主體性存在世界中出場的自然事物,研究存在層面上人與自然事物的關系,這是生態美學與生態科學的不同之處。第三,現象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現象描述和本質直觀,它們意味著現象學與美學有一種天然的內在聯系。第四,現象學探索的是人和世界的對象化關系形成之前的原初聯系,在這個原初存在的層面上來理解自然,讓我們看到人與自然事物的存在關聯遠比生態科學教給我們的要深邃復雜很多,生態美學將和科學一起培育對存在的敬畏之心①。
客觀地說,這四點都很有見地,的確都是生態美學構建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但是,王著對于生態科學的態度卻值得深入辨析。現象學的創立者胡塞爾出版過一本名著《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對于現代西方科學進行了嚴厲而深入的批判。王著之所以特別警惕“科學”(包括生態科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胡塞爾所批判的“歐洲科學”的具體所指及其所包含的思維方式。簡單說來,胡塞爾所批判的科學是以伽利略為代表的近代科學,這種科學思想將自然視為用數學語言寫成的一本書;其后的思想家們不僅將數理模式運用于自然,甚至試圖運用于正式社會領域。自然被理解為自然事情構成的總體即自然界,它可以、也必須采用實證科學所通常使用的實證方法來研究。在胡塞爾那個時代,生態學盡管早已出現但依然比較幼稚,在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也很微弱。但是,20世紀后半期以來,生態學取得了長足發展,目前已經成為眾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普遍借鑒的科學范式。特別是1935年出現的“生態系統”這個概念,有力地揭示了生物圈各個組成要素之間的內在關聯和運行規律,甚至將地球生態系統視為一個龐大的生命體。1972年出現的“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的核心思想認為,地球是一個生命有機體,其提出者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說過“地球是活著的!”這些自然觀與胡塞爾所批判的科學思想及其隱含的自然觀有著根本差異。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輕易否定科學,特別是不能輕易否定生態科學。在筆者看來,王著所提及的“生態文化”也必須與生態學科學聯系起來才能得以明確界定。所謂生態文化是指以生態學為基礎、符合生態規律的文化;如果沒有生態學,一切以“生態的”作為限定詞的概念諸如生態文化、生態文明、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生態文學等,都無法得到清楚的界定。
更為深層的問題在于,究竟應該如何看待現象學及其造成的所謂的“主體性框架”問題。王著明確斷言:現象學的全部研究都離不開“人的生存”這個充滿主體性色彩的框架,比如意識現象學研究的是在意識活動中事物的顯現,存在論現象學研究的是在人的生存實踐中世界的顯現,身體現象學研究的是身體知覺如何呈現事物,審美經驗現象學是從審美世界的層面來理解現實世界……總之,現象學在研究事物的時候絕不脫離“主體性存在”的框架,事物只有在這個框架中才能被呈現、被理解和被感知②。按照這種思路,王著甚至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論斷:“現象學不承認‘客觀世界’,只研究事物在先在的‘主體性存在’框架中的顯現”,王著將自己的立場稱為“堅定的主體性立場”①。
在筆者看來,王著的這個論斷值得進一步推敲。胡塞爾現象學特有的方法論步驟是“現象學的還原”,其基本方式是現象學的懸置。現象學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它看來,我們的自然態度預設了外部時空世界的實存,并預設了作為心理及肉身個體的我們自身的實存。現象學的懸置就是要把這種自然態度“放進括弧之中”。這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加括弧”這種做法僅僅是對于世界的客觀存在“存而不論”,以便更集中地探討世界如何在意識中被給予、被體驗,這絕不意味著否定世界的實際存在。即使這樣,現象學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很大分歧,比如現象學宗師胡塞爾與他最欣賞、最忠誠的學生英伽登之間關于觀念論(idealism)與實在論(realism)之間的論爭。胡塞爾的先驗觀念論認為,所謂的“真實世界”的存在與本質都依賴于先驗意識,它只由于意識才得以存在,意識之外則是“無”。英伽登盡管極其尊敬他的老師,但是從1918年起,他直接或間接地拋棄并批判其師的先驗觀念論,這種批判甚至貫穿在他此后整個哲學研究工作之中。
我們這里無法詳細討論現象學陣營內部的觀念論/實在論之爭,這里只是提出如下一個生態美學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否客觀地存在一個由生態學所描繪的客觀世界?在回答了這個問題之后,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第二個問題:這個世界是如何向人顯現其自身的?王著站在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的立場上,對第一個問題基本上“存而不論”,而是直接進入了第二個問題。筆者研究生態美學的立場首先是實在論的,然后才是現象學的觀念論的,原因在于,筆者認為生態美學是一種“對癥下藥”之論――它所針對的“病癥”是生物圈出現的生態危機,只有首先承認生物圈的客觀實在性及其生態危機的客觀實在性,生態美學的時代使命與思想主題才能得以確立。現象學對于生態美學研究的重大啟示在于,它讓我們極其清醒地意識到,客觀世界盡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并非直接呈現其自身的,而是通過人這個中介才得以顯現的。正因為這樣,人對于客觀世界的態度、顯現客觀世界的方式,才成為我們必須深入考察的課題。導致生態危機的原因多種多樣,人對于自然的態度、呈現自然的方式是其中最為深層、最為隱秘的。生態美學必須對此進行有理有據的分析批判。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同意王著的如下論斷:“生態美學與生態批評的獨特性就在于,它要基于人的存在這一主體性框架上展開對自然的研究,在人與自然事物的生存關聯中研究自然。”②
結語
篇4
[關鍵詞]生態美學;生態存在論;生態價值論;生態倫理學
[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3)02-0046-06
[作者簡介]岳友熙(1967―),男,山東高密人,文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省生態文化與循環經濟軟科學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學、美學、生態文化等研究。(山東淄博 255049)。
[基金項目]山東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基金項目(重大項目培育工程)“美國生態想像理論、方法及實踐運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曾受到山東省高等學校優秀骨干教師國際合作培養項目經費的資助。
Title: On Three Theoretical Bases of Eco-aesthetic Construction
Author: Yue Youxi
Abstract: Eco-aesthetic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lied subject of aesthetics which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aesthetic ideas. Eco-aesthetics is a new form of aesthetics based on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eco-environmental value theory, and eco-environmental ethics. It tak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eliminat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reaks the thinking way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and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eco-aesthetics; eco-existentialism; eco-value theory; eco-ethics
一、“生態美學”的基本內涵
所謂生態美學,主要是指生態學和美學聯姻而產生的一門學科,它是在當代生態觀念、環境觀念、美學觀念的啟迪下而產生的一門新興的跨學科性的美學應用學科。它是從美學的角度,用審美的態度、觀點和方法,研究人與自然的生態現象、生態關系和生態規律的科學。生態美學是生態本體論在美學領域的具體體現,具有很大的初創性和開拓性。生態美學不但注重對自然的定性(即存在的本性)研究,在對自然內在生命本質的考察中重構其哲學基礎,因此屬于物性論范疇,而且帶有更多的審美意味,注重對自然外在形式(即存在的表象)的觀照,因此屬于現象學的范疇。與此同時,它還更側重自然與人的現實生存關系,具體地說,就是以生態環境為中心,對自然進行價值定位和實踐再造(存在的價值)。生態美學覆蓋了人類對自然進行審美觀照的三個維度:即以真為美、以善為美、以美為美;包括以知性重解自然、以情感觀照自然、以意志再造自然等三種具體方式。
對生態美學來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審美觀。生態審美觀是一種全新的審美觀,它在自然審美上體現得最為突出:其一,生態審美觀的建構和形成,是以對“生態”的理解為前提的。這里所謂的生態,既不是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亦不是僅指單一的人與自然的自在狀態,而是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的整體化的系統聯系上。例如,德國美學家海德格爾所說的“在”的詩意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種生態審美的存在。其二,生態審美觀不是從生命的某一部分或生命的個體來孤立地、機械地看自然美的性質,而是從生命的有機整體、有機聯系來綜合審視自然美。其三,生態審美觀不單按照人的價值或者說自然的外在價值來看待自然美,而且也按照自然的內在價值來看自然美。自然美不單為人而美,也為其自身而美。其四,生態審美觀不單從自然人化的維度來看待自然美的產生,而且還從自然創化的維度來審視自然美的產生。大自然的進化,是一種自組織的進化。在大自然的自組織進化過程中,美是自然選擇的目的,是自然進化的方向。其五,生態審美觀不單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的內部心理等方面的統一來看待和諧,而且從整個宇宙,至少是從整個地球上生命的有序存在與運動來看待和諧,并賦予和諧以新的解釋與涵義。其六,生態審美觀不是將藝術美視為最高的美,而是將自然生態美視為最高的、典范的美。生態哲學中生態本體論的宇宙觀,意味著哲學思想的一場革命,生態美學中生態審美觀,也將全面地重塑人的觀念,徹底刷新人的生活。這是人類思想領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人類思想的巨大進步。
生態美學以“生態環境美”范疇的確立為核心,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的生態審美創造為目標,以期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相互和諧、真善美相互統一的自由審美人生境界。生態美學體現了生態文明時代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現實關注,以及對人類的終極關懷。這種生態本位的審美觀,既來源于對中國古老的傳統生態哲學深層智慧的開掘,又來源于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有機統一觀念的借鑒;既是對傳統美學審美觀的超越與挑戰,又為我們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美學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好契機。
二、生態美學構建的哲學基礎
生態美學是以生態存在論為哲學基礎的美學。“生態存在論”主要是建立在“存在論”哲學、生態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的新型理論,它肯定存在是世界本然的存在狀態和方式,反對在現實世界之外尋找存在的本質和依據;主張結合古代直觀整體論和當代生態科學、復雜性科學的成果,將存在理解為包含人、社會在內的整個大自然的存在,即把存在看作是由“人―社會―自然”組成的“三位一體”的統一有機系統整體。“生態存在論”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生態存在論繼承了系統論的整體性特征,認為生態存在不是人、社會和各種其他自然事物的零散的存在,而首先應當是整體性的存在。它在肯定人、社會和各種自然事物等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構成生態存在整體的基礎上,否定生態存在整體等于各部分事物和人簡單相加之和的機械觀念,堅持生態存在系統具有自身特定的質,是由人、社會和各自然事物等內在各要素之間非線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生態整體;特殊生態系統又存在于更高一級生態系統環境中,受更高一級生態系統規律、狀況、發展趨勢的影響,這種生態系統的整體特性就是其從所處系統環境中獲得的質的規定性。第二,生態存在論認為,人、社會和各種自然事物的生態存在具有有機性,它們是有機系統整體。它從生態科學觀念出發,肯定人、社會和各種自然事物的生態存在的有機性,而且把有機性理解為生命、生態系統自身具有的自組織、自調節、自選擇能力,把整個世界描繪成由人、社會和各種自然事物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協調、不斷進化的有機的統一體。第三,生態存在論認為,人、社會和各種自然事物的生態存在具有過程性。從自組織理論出發,把存在如實地描述為關系性的、過程性的和實體性的存在的統一,把自然生態過程視為統一的自組織運化過程,堅持不同層次的“實體存在”、不同層次事物之間的聯系都是在統一運化過程中形成、演化的觀點。①
“生態存在論”是建立在生態科學、復雜性科學理論發展的基礎上的新型理論,是對科學理論的概括和升華。它是對近現代機械論世界觀、傳統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否定,是在更高層面上對古代有機整體論的揚棄和復歸。“生態存在論”包括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和自然觀,是建立生態美學的哲學基礎,是生態文明時代精神的必然產物。生態美學就是“生態存在論”哲學在社會實踐領域的具體應用。以“生態本體論”為基礎的生態美學作為一種新的美學范式,是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有機統一的新的科學的美學范式。生態美學針對現代性過分強調自然的人化,把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偏頗,還強調人的自然化,重視自然生態規律,把人作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存在和演化規律;同時,生態美學又肯定人與自然萬物的差別,肯定人的主體性,肯定人的認識實踐能力和人的智慧,肯定生態美學建設是建立在人的現實認識實踐基礎上,主要依靠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認識、反思、協調和重構。生態美學的產生和發展是歷史的必然,是人類對消除人與自然關系嚴重異化要求的時代呼喚,是生態本體論時代的精神體現。
三、生態美學構建的價值論基礎
生態美學是以生態環境價值論為基礎的美學。生態環境價值論,就是人類在生態本體論時代對人與自然萬物及其生態系統的價值關系獨特新穎的基本看法和觀點。它主要是針對近現代人類本體論時代的主觀主義工具價值觀,肯定價值的客觀存在,重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和生態環境系統的價值,并重新闡述人與生態環境的價值關系。生態環境價值論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對傳統的價值論進行反思,在新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新型價值論。它從價值論的學術框架出發,對生態系統、人的生態環境以及其中多樣化生物的價值進行探討,結合生態保護的要求改造已有的價值論或為價值論提供新的內容。它是對人類本體論時代價值觀的突破和超越。生態環境價值論主要是哲學、文化意義上的價值論,主要探討的是價值的本質、價值的具體表現形式等問題。它在首先承認人是自然界當中具有自主性、獨立性和主觀能動性的特殊存在的基礎上,肯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價值,肯定人和自然萬物及其生態環境系統都具有自身存在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并認為它們都可以成為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它們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既有區別,又是內在統一,即兩者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同時,它還確定了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生態環境價值論的核心內容集中體現在對“生態環境價值”和“生態環境的價值”兩個概念的內涵的討論當中。所謂“生態環境價值”,就是指人與周圍的生態環境所構成的生態環境系統所具有的自身內在的有機價值。它是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包括人)天生地就具有消納廢物、維持生命和調節平衡的生態價值,是生態環境系統維護生態環境系統自身穩定、完整和美麗而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它反映的是人與周圍的生態環境具有本源性和本然性的聯系。而所謂“生態環境的價值”,在廣義上是指生態環境系統及其要素對其周圍的其他要素(包括人、自然事物、子系統、母系統等)的生存和發展所具有或體現出來的外在價值或工具價值;在狹義上,則是指生態環境系統及其要素對人的生存和發展所具有或體現出來的外在價值或工具價值,即只是相對人來說的。“生態環境價值”和“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兩個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是相互對立的。然而,它們兩者之間的關系又是內在統一的。①
生態環境價值觀是對宇宙本體論價值觀的補充和發展,是對人類本體論價值觀的突破和超越,它是生態環境美學賴以產生和形成的價值論基礎。傳統哲學認為,價值客體可以是自然物、人創造的財富,也可以是社會、組織和個人;但是,價值主體卻只能是個人、群體和社會,或者說只有人才有資格成為價值主體。這種人類本體論價值觀的偏頗和現代科技的片面發展,給“人――自然――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障礙。因此,人類需要重新反省自身的價值觀,繼承和發展傳統儒家“贊天地之化育”之精神,在自身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不但肯定人是生態環境價值主體,而且強調其他生態環境各要素也可以作為生態環境的價值主體;不但要考慮到人類自身的目的和價值,而且也要考慮到其他生命體、生態環境系統、生物圈的內在價值,從維護和促進生態環境系統和地球生物圈的生存和發展高度,把自身的內在價值最大限度地轉化成對生態環境系統和生物圈的工具價值,在人與生態環境系統共生共榮、協調發展的基礎上,使自身的內在價值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實現。從生態環境價值論來看,價值主體的內容已經突破了傳統的理解,認為生態環境系統各要素都可以成為生態環境價值主體。生態環境價值觀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把人類由世界的主宰變成了生態環境系統當中的普通一員。人類在利益上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人類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人類由人類本體論時代轉向了生態本體論時代,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人類的價值觀發生了徹底轉變,即由人類本體論價值觀轉向了生態環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以價值主體超越了傳統價值觀的評價主體,認為價值主體不單是人,也可以是人之外的其他生態環境要素。生態環境價值觀不但從認識論角度,在肯定人的獨立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強調了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價值的對立統一關系,而且還從生態存在論角度,把人與其周圍的生態環境系統看作一個最大的完整的生態環境總系統,肯定了這個生態環境系統的內在的有機的生態環境價值。并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的價值與生態環境價值是辯證統一的。它認為生態環境價值和生態環境的價值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都是生態環境系統進化的結果。生態環境系統的各個因素都對維持生態環境系統的完整與和諧做出了貢獻,因此都具有生態環境的價值。作為人類的文化現象,生態環境價值是人類超越自我,借助人的洞察力對生態環境價值關系進行分析的產物,不是人類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價值的判斷和評價,而是將人類自身融合于生態環境系統當中的整個生態環境系統的存在價值和內在價值。生態環境價值論的提出使人類對自己的主體地位進行反思,迫使人類矯正自己對待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的態度和行為,這對保護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生態環境系統的利益具有重大意義。①生態美學就是以這種生態環境價值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新型美學。
四、生態美學構建的倫理學基礎
生態美學是以生態環境倫理學為基礎的新型美學。“生態環境倫理學”也被稱為“生態倫理學”,是一種主張把道德關懷(moral consideration)擴展到人之外的各種非人類存在物身上去的倫理觀點和學說。它是在對傳統倫理學進行反思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它的繼承、發展和超越。其理論核心是承認各種非人類存在物擁有獨立于人類的“內在價值”及人類必須予以尊重的“生存權利”,并把它們的這些內在價值和生存權利(而非人類的利益)作為判斷人們對它們的實踐行為在道德上是否正確的終極標準,作為對人的實踐行為進行善惡評價的重要依據。②這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新型的倫理思潮或價值觀。生態倫理學的革命性和新穎性,主要體現在它肯定了各種非人類存在物擁有獨立于人類的內在價值和人類必須予以尊重的生存權利,空前地擴大了“道德共同體”或“道德聯合體”(moral community),為今天我們正確理解“人――社會――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提供了新型的道德根據。③生態倫理學將道德共同體擴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無生命的存在物,突破了傳統倫理學對人的固戀(fixation),把倫理學的視野從人類擴展到了更寬廣的大自然,使道德聯合體(moral community)的范圍從人類自身擴展到人類之外的其它非人類存在物,從而拓展了倫理學的范圍,使其實現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飛躍。這種把道德共同體擴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無生命的存在物的倫理思想,就是傳統的自由主義的終結和新的自由主義的開山。④
生態倫理學是一種具有不斷開放性的倫理學,它要求人類應該有一種偉大的生態倫理情懷:對他人的關心,對動物的憐憫,對生命的愛護,對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他應當與某種永恒的東西“照面”,把生活的意義與某種比個人更宏大的過程聯系起來。這種永恒的東西和偉大的過程就是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和綿延不絕,就是大自然的完整、穩定和美麗,就是上蒼之“大生”和“廣生”之美德。我們甚至認為,由于大自然或地球是所有事物的“生命搖藍或生養環境”(originating matrix or parental environment),所有的事物都是大自然創造的;哪里存在著積極的創造性,哪里便存在著價值。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倫理學僅僅限制在地球的范圍內,宇宙是我們所占據的地球的生命搖藍,我們應當把它也包括進最終的倫理王國中來,超越“地球中心論”或“地球沙文主義”,走向“宇宙倫理學”。⑤
生態倫理學在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權利平等的同時,還承認人類具有不同于自然的其它物種的特殊性,承認人類具有高于其它物種的特質,這種特質就是人類具有思維能力,有理性。而人的理性就表現為對自己行為的認知,對自己行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他能夠對自己的需求加以控制,能夠限制自己。當前,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已經向人類發出了嚴重的警告,我們應該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改變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人類的活動能夠與自然的存在相適應,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圓融共舞的共同體。⑥
生態倫理學就是我們建立生態美學的重要基礎之一,它在生態美學的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基礎地位和指導作用。它能夠幫助我們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突破主客對立的傳統思維方式,重建理性,重建主體性,重新認識自然的價值,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辯證關系,為我們保護生態環境和建設生態美學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盡管這種思想上的改變在越過一定界線以前很少有明顯的變化,但是,一旦關鍵的認識改變以后,巨大的變化就會像洪水般立刻涌現。我們的生態美學就會轟轟烈烈地建立起來,人類就會邁入真正的生態文明時代。
篇5
關鍵詞:孟子;新儒學;生態美學
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學日漸成為“顯學”。它作為中國較早地進行中西、古今文化融會思考的學派,不僅其價值得到肯定,更成為如今學者探索如何建構中國本土的現代文論、美學、哲學等的典型個案。新儒家學者以儒統莊,以儒統佛,以儒家精神會通西方思想,完成傳統文論、美學、哲學某種程度的轉型,形成不同于其他學者、學派的闡釋。就在這種闡釋的重建過程中,有一個值得當下美學界關注的現象,那就是三代新儒家學者已經自然而且必然地完成的“新儒家人文主義的生態轉向”:這種轉向最早體現在熊十力先生提出的發人深省的自然活力論,還有梁漱溟強調以調和折中的態度對待自然。再就是后來,臺灣、香港、大陸的三位領銜的新儒學思想家錢穆、唐君毅和馮友蘭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說,儒家傳統為全人類做出的最有意義的貢獻是“天人合一”的觀念。[注:參見杜維明《新儒家人文主義的生態轉向: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發》,載《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2期。]這一結論似乎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發現,但從他們對于此觀念所作的闡釋來看,這種發現也不是在復述傳統的智慧。事實上,他們不僅是在回歸那個他們鐘愛的傳統,也是為了當下的需要來重新理解這個傳統。如果說新儒學的生態轉向在一開始還不是有意識的,那么到了杜維明這里,則已完全成為一面明確的旗幟。他接著第一、二代新儒學往下講,不僅完成了所謂“生態轉向”,并且還將這一轉向帶進對中國美學的全新思考。
一、中國藝術精神里的人格修養
在現代新儒家三代學者中,第二代臺港新儒家的徐復觀對藝術和美學探討較多,并且有著自己較為系統的美學思想,這集中體現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他認為,在中國哲學和歷史上,《莊子》集中體現了審美主體性在中國的誕生,而儒家思想中所確立起來的道德主體性,同樣充滿著深刻的美學內容。徐氏主要探討了莊子與孔子的美學思想,但卻很少提及孟子。杜維明先生正是看到了孟子在中國美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特撰文接著徐復觀往下講,為《中國藝術精神》補充了一個“續篇”。
杜維明先生在《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觀念:中國美學探討》一文中集中考察孟子的修身觀念是如何同中國藝術理論相關聯的。他開篇即說道:“徐復觀先生在他的《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指出,儒家和道家都確信自我修養是藝術創造活動的基礎,這與藝術的根本目的是幫助人們去完善道德和精神的品格的陳舊觀點恰恰相反。它提出了一條解答藝術本身是什么,而不是解答藝術的功能應當是什么的思路。在這個意義上,藝術不僅成了需要把握的技巧,而且成了深化的主體性的展現。”280他正是順著徐先生的這一思路去進一步闡發孟子的修身觀念的。
欲了解杜維明的美學思考,先應明確徐復觀是如何闡釋“修養”與中國美學的關系的。徐復觀所說的“修養”,乃是一種“人格修養”,是指“意識地,以某種思想轉化、提升一個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體的人格”[2]362。中國只有儒道兩家思想,由現實生活的體悟和反省,迫近于主宰具體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潛德的顯發轉化生命中的夾雜,而將其提升、純化,轉而又落實于現實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價值的基礎。所以,徐氏認為,只有儒道兩家思想,才有人格修養的意義。
徐復觀強調,人格修養常落實于生活之上,并不一定發而為文章,甚至也不能直接發而為文章。因為就創作動機來說,人格修養并不能直接形成創作的動機;就創作的能力來講,在人格修養外還另有工夫。同時文學與藝術創作,并非一定有待于人格修養。但人格修養所及于創作時的影響,不像一般所謂思想影響,常是片斷的、緣機而發的,它是全面的、由根而發的影響。而當文學藝術修養深厚而趨于成熟時,也便進而為人格修養。另外,作品的價值與人格修養有密切關系。徐復觀指出:“決定作品價值的最基本準繩是作者發現的能力。作者要具備卓異的發現能力,便必須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須有卓越的人格修養。中國較西方,早一千六百年左右,把握到作品與人的不可分的關系,則由提高作品的要求進而提高人自身的要求,因之提出人格修養在文學藝術創造中的重大意義,乃系自然的發展。”一言以蔽之,人格修養與藝術在最高境界上有其自然的結合,具有共生性。儒道兩家所成就的人格修養,不止于文學藝術的根基,但也可以成為文學藝術的根基,一旦發而為藝術精神的主體因素,便對中國藝術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進而主導著中國藝術發展的總體方向。在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必以人格的修養、精神的解放為技巧的根本,為境界的根本,正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卷10。因此,徐復觀在對傳統藝術活動的考察中所發現的人格修養與藝術的這種微妙的關聯,乃是中國藝術精神的特質所在。
綜觀中國古典美學,自孔子始,審美一直與修養有著根本的聯系。中國美學講境界,藝術以境界為最上。正如王國維所說:“(詞)有境界則自成高格。”(不惟詞如此,中國其他藝術皆如此)而修養的歸宿即是境界。由修養而達境界,此一境界,既是人生境界,亦是審美境界。在中國古人那里,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何以相通?在現代人的生存境域中,世俗的人生何以成為審美的人生?杜維明先生有進一步的挖掘。
二、孟子修身觀念的生態美學精神
徐復觀告訴我們,要想真正了解中國藝術精神,必須從修養的工夫透進,方能得其三昧。杜維明顯然認同這一結論,因而才順著這種美學研究的方向,去挖掘孟子修身觀念中所蘊涵的現代美學精神。那么,杜維明進一步闡發“修身”的出發點是什么,他是如何理解“修身”的,他對“修身”作了怎樣的引申,引申的意圖何在呢?
首先,他澄清,自己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探究與道家美學所不同的,或是作為道家美學之補充的儒家美學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想盡量開發這兩種傳統學說所共有的象征符號資源。他明確指出:“把徐先生的分析推進一步,我認為,把修身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比起人們試圖系統地將傳統分梳為道家和儒家來說,也許出現得更早些”,“儒家強調的人文主義,也許初看起來與道家的自然主義相沖突。但是,按照他們對自我修養的共同關注,我們不能說儒家堅持社會參與和文化傳承與道家追求個人自由不相容。道家批評儒家的禮儀,儒家批評道家的避世,都體現一種對話式的交互作用,它反映出兩家之間存在著更深沉的一致”。可見,杜維明并不是要論證孟子同中國美學有著什么特殊的關系,而是要借孟子思想生發出中國美學整體的特性。再者,他的直接目的是想通過詮釋的重建去發現隱含在孟子思想里的藝術理論,進而指出某種銜接傳統與現代的美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杜維明所用的“修身”這個概念,并不是僅僅對于人的形體而言。修身的內容實則比形體的轉化要豐富得多。“身”只是一個含意有限的形象說法,非英文“body"可以代替,它其實象征了整個自我,乃儒家文化中極其豐富和莊嚴的符號。所謂修身,即修己,包含了自我轉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過程。比之徐復觀所說的“人格修養”,“修身”有著更為廣闊的涵義。“人格修養”容易被人們作為純粹的道德操練來理解。自孔孟以降,后世的一些儒者確有此一傾向。事實是,人們一直用一種不太恰當的“手段”與“目的”的用語來描述藝術與人格(修養)之間的關系,而這種表述卻模糊了二者的共生關系。但是,如果我們將人格修養擴展為杜維明所說的“修身”來理解,那么它與中國藝術的特殊關聯就會變得更加明朗,甚至可以說,“修身”就是中國藝術精神的根本。藝術也由此可以理解為“深化的主體性的展現”,這是傳統中國所特有的一種“大藝術觀”。
孟子的修身觀念包含兩個方面的深意:一方面,“大體”與“小體”的和諧發展。在孟子看來,心為“大體”,身體只是“小體”。修身就是要使“大體”而不只是“小體”得到發展。一個向學生傳授六藝的儒學大師,必定要認識到六藝既是需要操習的動作,又是應從精神上去掌握的科目。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一個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在轉化過程中的身心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在人的身、心結構中,存在著將自我發展為與天地合一的真正潛能。修身更重要的是為了體驗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共鳴。“大體”可以“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盡心上》,但它歸根結底只不過是本真的人性。修身就是要將本真的人性顯發出來,而美的實現則需要這種修身的工夫。所以,儒家的修身方法不僅具有社會學的意義,也具有美學的意義。古人通過修身所實現的人生境界,自然就有審美境界的生成。
進一步引申,修身所體現出的實質上是一種生態美學精神。生態美學本是一個現代范疇。在21世紀初的中國美學界,引起最多關注和爭論的就是這個范疇。它作為美學的一種新理論或者方法,更多地凸顯出傳統與現代銜接和轉化的可能性。因此,強調修身體現生態美學精神,其實就是對修身作一種新的現代的理解和轉換。生態美學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自身處于生態平衡的審美狀態,提倡綠色的人生,審美的人生。而孟子的修身觀念則明確表示,人首先要實現自身的和諧,才能與天地合流。生態美學強調整體性,而孟子在關注整體性的同時,還看到了“整體”中的“根本”,那就是人自身的生態和諧。事實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生態平衡確實依賴于人本身對待外物的態度和方式,此一態度和方式則根源于人的認識和精神境界。人必須從自身做起,修身是一種重要途徑,它不僅導向生態平衡,也直指審美的和諧人生。它作為自我轉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過程,不僅是孟子所倡導的,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大學》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如果我們用現代話語來解讀中國傳統之“修身”理念,其實它就是“精神生態”。由此,它將給予中國當代的生態美學研究以重要的啟示。
三、杜維明給予生態美學研究的啟示
在孟子那里,與修身一樣,美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由于將修身作為理解美的觀念的參照點,因而“美”很難成為一個完全客觀化的靜態范疇,它與善、與真一樣,都是人不斷成長中出現的品質,它們作為一種激勵人心的鵠的而存在。“充實之謂美”。“當美塑造著我們的充實感時,不是作為一種固定的原則,而是作為正在體驗生命的自我,和所感知的實體對象之間的一種動態的相互影響而起作用的。我們在事物當中看到了美。在描述美的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從外在的物質形體轉向內在的生命力,最后達到無所不包的精神境界”。修身包含著主體的自我轉化,而這種自我轉化無論在美的創造或欣賞中,都是美的真正基礎。在主體的自我轉化這一環節上,杜維明拈出兩個重要概念:“相遇”和“聽的藝術”。這更加表明他在有意識地以生態美學的眼光來解讀和發現古典。
相遇。杜維明說:“我們欣賞的對象可能是一棵樹、一條河流、一座大山或一塊石頭,但是,我們感受到它們的美,使我們覺得它們并不是毫無生氣的對象,而是一種和我們活生生的相遇。確切地說,是一種‘神會’”。杜維明用“相遇”來指稱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的關系,來形象地表征古典美學里物我的神會,正是為了說明,中國傳統美學里并沒有主客二分,古人不會把自己的人格強加于外在世界,《孟子》關于人的思想并不是一種人類中心論,就其終極意義而言,它旨在表明人的自我轉化首先體現為一種態度的轉變,而人的自我實現則取決于人與自然的互動。正像徐復觀先生所說的:欲“成己”必需“成物”,而不是“宰物”、“役物”。
20世紀著名的猶太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認為,人生與世界具有二重性:一是“為我們所用的世界”,一是“我們與之相遇的世界”,可以用“我—它”公式稱謂前者,用“我—你”公式稱謂后者。布伯所謂“我—它”的范疇,實指一種把世界萬物(包括人在內)當作使用對象,當作與我相對立的客體的態度;所謂“我—你”,實指一種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與自己同樣獨立自由的主體性的態度,此時,在者于我不復為與我相分離的對象。[注:參見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7-21頁。]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中,即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筑居于“它”之世界,但人也棲身于“你”之世界。人對“你”的熾熱渴念又使人意欲反抗“它”、超越“它”,正是這種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與藝術。布伯說:“人無‘它’不可生存,但僅靠‘它’則生存者不復為人。”布伯的學說直接針對西方思想史上兩種居于支配地位的價值觀。雖然他的目的在于闡釋宗教哲學的核心概念“超越”的本真涵義,以及澄清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愛心,但他對人生態度的兩種概括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具有普遍性的。
生態美學批評現代人類的實用主義和功利性,痛斥他們將“我—它”關系加以絕對化和極端化,著眼于“我—你”關系的和諧建構和擴展,因為只有后者才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和無間,人與社會的和諧融洽。如果我們把人與世界的關系概括為主要的三種形態:認知的、實踐的和審美的,那么大家就會發現,前兩者所體現的其實就是布伯所稱的“我—它”關系,而審美所呈現的則應該是“我—你”關系。我與你相遇,“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無須有待于他物,我當以我的整個存在,全部生命和本真人性來接近“你”。最終“我”與“你”都升華了自己,超越了自己。這便是杜維明先生所說的“神會”,亦是孟子修身觀念的真諦所在。因此,“我”與“你”的相遇,是審美的相遇,亦是生態精神的呈現。正如杜維明先生在《存有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心“對自然的審美欣賞,既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占有,也不是主體強加于客體,而是通過轉化與參與,把自我融入擴展著的實有”。“我”在展開審美體驗時,漸漸忘記了“我”的存在,完全“化”入“你”的體內,以“你”的存在為自己的存在,逍遙游于“我—你”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即是審美化境,是生態美學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所發現的生態特征。物我合一的境界真正是中國藝術精神的體現。杜維明還指出,對于人與自然的這種互通性和親切性的審美體驗,往往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我修養的結果,“返回自然的過程不僅包含著記憶,而且也包括‘絕學’和遺忘。我們能參與自然界生命力內部共鳴的前提,是我們自己的內在轉化"。這種觀點與徐復觀先生對“心齋”的修養工夫的解釋是一致的。可以這樣說,中國古典美學是一種以修養為基礎和工夫的“相遇”美學,此一“相遇”,則真正體現了深刻的生態美學精神。
聽的藝術。藝術感動并影響著我們,古人們相信,它來自人與天地萬物共有的靈感之源。講到聽的藝術,很多人馬上會想到音樂。這當然是沒錯的。但除此之外,它在這里更蘊涵深一層的隱喻。“聽”具有生態層面的重要意義。
聽覺的感知作用在先秦儒學中占重要地位。杜維明相信:“如果我們將眼光盯著外部世界,那么,儒家之道是不可得見的;如果僅僅依靠視覺形象化這種對象化活動,是不能把握宇宙大化的微妙表現的。誠然,像舜這樣的圣王,能夠通過對自然之微妙征兆的探索來洞察宇宙活動的初幾。但是,我們卻是通過聽的藝術,才學會參與天地萬物之節律的。‘耳德’或‘聽德’,使我們能夠以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欣賞的、相互贊許的方式去領悟自然的過程。”生態美學一直在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拋棄西方的二分法思維模式,在中國傳統生態智慧中發掘這種主體對待自然的審美的態度。因為此一審美的態度真正消融了主客二分,體現了物我的平等、和諧、共融。杜維明先生認為先秦儒家是經過身心的修養將自己開放給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通過拓展和深化自己的非判斷性的接受能力,而不是將自己有限的視野投射到事物秩序上,才得以成為宇宙的共同創造者。
聽的藝術除了可以表明態度以外,還聯系著特殊的感受和表達方式。“聽的藝術”里所說的“聽覺”,并不是指人的生理聽力,而是指人的感受能力。正如馬克思曾經說的,要理解音樂,必須具有“音樂的耳朵”。那么,要聽懂自然,就必須具有親和自然、體悟自然的能力。聆聽與傾訴相對,自然之中自有天籟,天籟即是自然生命的傾訴。面對自然的私語,我們只能閉目傾聽,用聽來交流,用耳來感受。正如佛祖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惟迦葉破顏微笑一樣,聽的藝術正是這種無需言語的心靈默會。所以,莊子也用“聽”來描述他的“心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莊子·人間世》。此乃莊子的修身之法。在聽的過程中,我們不再是外在于自然的主體,而成為各種生命力內部共鳴的息息相關的一部分。在聽的過程中,我們成為各種生命力內部共鳴的息息相關的一部分。不僅莊子重視“聽”,孔子更是以音樂這種聽覺藝術來實現他的人生境界。所以孟子才會選擇音樂作為隱喻討論孔子之圣性:“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孟子·萬章下》而代表人格發展至高峰的“圣”字之古體“圣”,即以耳為根。可以這樣說,聽,體現了生態學的關系原則,“聽德”其實是中國藝術共有的特點,因而中國藝術是體現著生態精神的偉大藝術。
更進一步講,“聽”在古人那里也是一種表達方式。聽者無言,無言與有言相對,因此也是表達方式之一種。無言甚至更勝于有言,只有無言才不會咄咄逼人,才會以欣賞的姿態和審美的眼睛“傾聽”自然。有言則容易陷入主觀,破壞物我的相融、天人的合一。所以才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說。所以才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說。因為無言就是沒有明確的語意,于是也就具有感受的無限可能性。有言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藝術的限制,言是表達的媒介和形式,有媒介和形式便是有隔,便是有限,否則便是不隔,便是無限。
無言和聽的藝術都是一致的,它們象征著精神的自由和無限,表達了“我”對“你”的尊重,體現了平等和共存。因此,“聽”開啟了生態學意義上的關系原則,聽的藝術則呈現了生態美學的精神。
綜上,我們通過對杜維明先生關于孟子思想的詮釋的分析,可以較顯明地看到杜先生通過詮釋所要指出的美學研究方法。首先,正如徐復觀對人格修養的關注一樣,杜先生進一步整理、闡發了先秦儒學、特別是孟子的修身觀念,并進而得出結論:從修身、修養來理解中國古典美學,更容易觸到中國藝術的本質,此處儒、道藝術精神之分則不顯;再者,正如道家學說里存在著豐富的生態思想一樣,先秦儒學、尤其是孟子關于人的思想同樣開啟了一種現代意義上的生態精神。修身這一觀念本身所包含的人自身、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正是生態美學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存狀態。這足以表明,生態學的視野和方法必定為中國美學帶來更大的言說空間。
在中國大陸學界,生態美學自2000年以來逐漸成為美學研究領域的新熱點,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美學研究的視野。然而眾多生態美學的提倡者們卻未曾注意到,杜維明這個海外學者早在90年代就已經提出將生態的方法運用到美學研究中來并表達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文將杜氏觀點進行整理和生發,一方面是想引起生態美學研究者們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對生態美學研究的一種探索。
[參考文獻]
[1]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M]∥郭齊勇,鄭文龍.杜維明文集:第3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2]徐復觀.儒道兩家思想在文學中的人格修養問題[M]∥李維武.徐復觀文集: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3]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4]王國維.人間詞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5]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