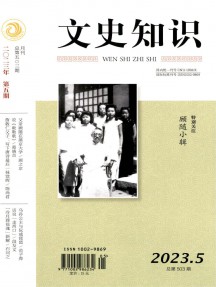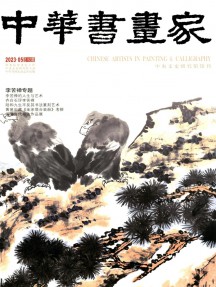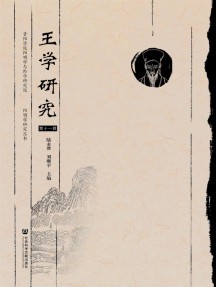古代文學(xué)通論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shí)間:2023-10-13 15:36:54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shí)的探索者,寫(xiě)作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古代文學(xué)通論,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關(guān)鍵詞:古代漢語(yǔ) 文化傳承 漢字 文史知識(shí)
古代漢語(yǔ)是高校中文專業(yè)的一門(mén)基礎(chǔ)課程,其涵蓋的知識(shí)相當(dāng)廣泛,包括文學(xué)、歷史、哲學(xué)、語(yǔ)言學(xué),還涉及天文、律歷、姓氏名號(hào)、禮儀風(fēng)俗、車(chē)馬宮室、職官地理等相關(guān)知識(shí),這些內(nèi)容本身就是我國(guó)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所在。當(dāng)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yáng)已經(jīng)上升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指出:“體現(xiàn)一個(gè)國(guó)家綜合實(shí)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shí)力,這事關(guān)一個(gè)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浩如煙海的中國(guó)文化典籍蘊(yùn)含著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寫(xiě)成,古代漢語(yǔ)課程的主要講授對(duì)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課堂教學(xué)中,必須把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體現(xiàn)出來(lái),以實(shí)現(xiàn)古漢語(yǔ)教學(xué)的文化傳承功能。現(xiàn)結(jié)合筆者的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對(duì)如何在古代漢語(yǔ)教學(xué)中傳承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從漢字入手,注重解析語(yǔ)言文字所蘊(yùn)含的文化內(nèi)涵
中華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沒(méi)有斷流的文化,漢語(yǔ)漢字不僅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其本身也是中國(gu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若能利用漢字表意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結(jié)合字形分析,不僅能讓識(shí)記古詞匯的過(guò)程更容易,同時(shí)也能讓學(xué)生從中了解中國(guó)語(yǔ)言文字所蘊(yùn)含的文化內(nèi)涵,因?yàn)閷?duì)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從漢字入手了解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以下略舉幾例。
1.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宮室建筑。
《周易系辭下》(包犧氏之王天下)載:“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宮室。”《說(shuō)文》:“穴,土室也。”字形從“宀”,像房頂,下應(yīng)為“凵”,組合起來(lái),其實(shí)“穴”是一個(gè)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狀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頂。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竅皆為穴。”《說(shuō)文》:“宮,室也。”徐復(fù)《說(shuō)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據(jù)半坡圓形房屋遺址復(fù)原,其房屋乃在圓形基礎(chǔ)上建立圍墻,墻之上部覆以圓錐形屋頂,又于墻中部開(kāi)門(mén),門(mén)與屋頂斜面之氣窗孔呈‘呂’形,此種形制房屋,屋頂似穹廬,墻壁又似環(huán)形圍繞,故名為宮。”
通過(guò)字形分析可見(jiàn),最初人們是選擇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來(lái)發(fā)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來(lái)才有地面式建筑。
《晉靈公不君》載:“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guò)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這里有兩個(gè)動(dòng)作“登”“下”“趨登”,教材注釋:“快步走上堂去。”那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說(shuō)呢?“堂”,《說(shuō)文》:“堂,殿也。從土,尚聲。”字形從“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yàn)榈貏?shì)較庭為高,所以有階,進(jìn)入堂就有一個(gè)登階的過(guò)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語(yǔ)有“登堂入室”,文選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說(shuō)。
2.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車(chē)戰(zhàn)。
《燭之武退秦師》載:“晉軍函陵,秦軍錟稀!苯灘淖⑹停骸熬,用如動(dòng)詞,屯兵。”《說(shuō)文》:“軍,圜圍也。四千人為一軍。從車(chē),從包省。”段玉裁注:“包省當(dāng)作勹,勹,裹也。,勹車(chē),會(huì)意也。”“軍”是個(gè)會(huì)意字,從“勹”從“車(chē)”。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從》:“字從車(chē),從勹,會(huì)意。古者,車(chē)戰(zhàn),止則以車(chē)自圍。”
古代以車(chē)戰(zhàn)為主,以戰(zhàn)車(chē)為中心,一輛戰(zhàn)車(chē)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稱一乘。軍隊(duì)駐扎時(shí),用兵車(chē)作為掩體,圍繞在軍隊(duì)駐扎地的周邊。所以,“軍”可作動(dòng)詞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詞。
3.從漢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禮儀。
《晉靈公不君》有“稽首”這種禮節(jié),如何行禮?《說(shuō)文》:“稽,留止也。從,從尤,旨聲。”“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廣居《疑疑》:“,木之曲頭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滯人。此三體會(huì)意也。”可見(jiàn),“稽首”這種禮節(jié)在行禮時(shí),頭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時(shí)間以示尊敬,應(yīng)當(dāng)是一種比較鄭重的禮節(jié)。
二、合理補(bǔ)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識(shí)的講解,促進(jìn)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
古代漢語(yǔ)文字繁難,學(xué)生很容易有畏難情緒,常常是學(xué)生學(xué)得苦,教師教得累。若能將生澀的文言文放在豐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僅能夠使學(xué)生加深理解,讓課程妙趣橫生,更能促進(jìn)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以下略舉幾例。
1.適當(dāng)補(bǔ)充相關(guān)歷史背景的介紹。
《宮之奇諫假道》載:“晉侯復(fù)假道于虞以伐虢”“復(fù)”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學(xué)生追問(wèn):“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時(shí)候?”教師就需要補(bǔ)充《左傳?僖公二年》所載:“晉荀息請(qǐng)以屈產(chǎn)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duì)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qiáng)諫,且少長(zhǎng)于君,君昵之,雖諫,君將不聽(tīng)。’乃使荀息假道于虞。”從中,學(xué)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經(jīng)過(guò),也對(duì)虞侯的貪婪以及宮之奇勸諫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齊桓公伐楚》載:“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齊桓公伐楚,為什么要侵蔡呢?補(bǔ)充《韓非子?外儲(chǔ)說(shuō)左上》中的有關(guān)記述:“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fù)召之,因復(fù)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guó),功業(yè)不可冀也,請(qǐng)無(wú)以此為稽也。’桓公不聽(tīng)。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為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tīng)從。因遂滅之。此義于名而利于實(shí),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bào)仇之實(shí)。’”通過(guò)《韓非子》的記述,我們既了解了文選所記事件發(fā)生的歷史背景,同時(shí)對(duì)管仲的深謀遠(yuǎn)慮也有了初步的認(rèn)知。
2.適當(dāng)補(bǔ)充相關(guān)風(fēng)俗的講解。
《段于鄢》載:“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武公在申地娶女子為妻,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風(fēng)俗。鄭國(guó)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個(gè)諸侯國(guó),鄭國(guó)最早的諸侯是鄭桓公,他是周厲王的小兒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鄭國(guó)以“姬”為姓,這就意味著,鄭國(guó)的諸侯不能從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諸侯國(guó)娶妻。而申國(guó)為姜姓國(guó),符合異姓通婚的風(fēng)俗習(xí)慣。
《觸龍說(shuō)趙太后》載:“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有學(xué)生奇怪,為什么要握著腳后跟哭泣呢?據(jù)劉向《說(shuō)苑?修文》的記載,古人親迎時(shí),男方要帶上“屨二兩”即鞋兩雙到女家,出嫁女的母親要在夫家送來(lái)的兩雙鞋子中取一雙給女兒穿上,然后整理女兒的發(fā)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時(shí),母親就要作最后的叮囑,讓女兒善待公婆,對(duì)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萬(wàn)“無(wú)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辭母親,母親在房門(mén)口親自把女兒交給女婿。接著,女兒在堂上拜辭父母,在大門(mén)口拜辭諸母,最后隨夫上車(chē)。“持其踵為之泣”正是母親“取一兩屨以履女”時(shí)一個(gè)很自然的動(dòng)作。因?yàn)橐H手給女兒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為之泣”就是一邊給女兒穿鞋一邊叮囑說(shuō):“無(wú)敢回也”。
3.適當(dāng)補(bǔ)充相關(guān)禮儀的講解。
古人的見(jiàn)面禮分為揖、拜、稽首等。這些見(jiàn)面禮在文選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不加區(qū)別,對(duì)理解文選會(huì)有較大的影響。揖,又稱揖讓,是最普通的見(jiàn)面禮,行禮的時(shí)候,左右手食指中指無(wú)名指小指并攏,左掌與右掌背交叉或平疊,掌心向內(nèi),左右拇指相扣,兩手合抱于胸前,拱手為禮。這種禮節(jié)多用于文官。拜,也稱拜禮,古人一般拜兩次,稱為“再拜”,如《齊晉之戰(zhàn)》:“韓厥執(zhí)縶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jìn)。”這種禮節(jié)較揖禮更為恭敬,行禮時(shí),下跪后兩手拱合,低頭至手與心平。稽首則是最為恭敬的見(jiàn)面禮,多用于下級(jí)拜見(jiàn)上級(jí),晚輩拜見(jiàn)長(zhǎng)輩,臣子拜見(jiàn)君王。行禮時(shí),先拜,然后雙手合抱按地,頭伏在手前邊的地上,頭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時(shí)間以示尊敬,整個(gè)動(dòng)作比較緩慢。《齊晉之戰(zhàn)》所載“執(zhí)縶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jìn)”是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戰(zhàn)勝國(guó)的將領(lǐng)俘虜戰(zhàn)敗國(guó)的國(guó)君時(shí)所施的禮儀,手持絆馬索進(jìn)前,行再拜稽首之禮,恭敬地進(jìn)獻(xiàn)美酒。可結(jié)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所載:“子展執(zhí){而見(jiàn),再拜稽首,承飲而進(jìn)獻(xiàn)。”子展在俘虜陳侯時(shí)以同樣的禮儀對(duì)待陳侯。
4.適當(dāng)補(bǔ)充車(chē)馬制度的相關(guān)知識(shí)。
《齊晉之戰(zhàn)》提及齊軍和晉軍主帥所在的戰(zhàn)車(chē)以及車(chē)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們各自的職責(zé),對(duì)下文的理解就會(huì)有障礙。所以要補(bǔ)充古代戰(zhàn)車(chē)中位置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古人坐車(chē),以左為尊,所以戰(zhàn)車(chē)也是一樣,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馭;車(chē)右自然在右側(cè),手持長(zhǎng)矛或長(zhǎng)戟,除了保護(hù)尊者,防止敵人靠近戰(zhàn)車(chē)以外,還必須在車(chē)受到阻礙時(shí),讓車(chē)子順利前行,故而車(chē)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yàn)橹鲙浀膽?zhàn)車(chē)之上有指揮作戰(zhàn)的戰(zhàn)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車(chē)右仍然在車(chē)子的右側(cè)。
《齊晉之戰(zhàn)》還有“驂\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補(bǔ)充說(shuō)明駢、驂、駟。兩匹馬拉一輛車(chē)稱為駢,三匹馬拉一輛車(chē)稱為驂,四匹馬拉一輛車(chē)為駟。駕車(chē)的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驂馬和服馬之分,中間負(fù)責(zé)駕轅的,為服馬,兩邊的馬叫驂馬。
三、轉(zhuǎn)變觀念,采用多種先進(jìn)手段和教學(xué)方法,完成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
教師應(yīng)當(dāng)改變教學(xué)觀念,古漢語(yǔ)的教學(xué)不能僅僅停留在字、詞、句、語(yǔ)法等知識(shí)的講解上,更應(yīng)當(dāng)精心選取教學(xué)內(nèi)容,塑造學(xué)生的品格,注重弘揚(yáng)民族精神。如在講授《論語(yǔ)》《孟子》《禮記》等儒家經(jīng)典時(shí),要能結(jié)合當(dāng)前的大環(huán)境,引導(dǎo)學(xué)生理解古代為人處世的準(zhǔn)則:《論語(yǔ)?學(xué)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養(yǎng);《論語(yǔ)?微子》中“我行我義”的精神風(fēng)范;《禮記?教學(xué)相長(zhǎng)》中通過(guò)不斷學(xué)習(xí)來(lái)發(fā)現(xiàn)不足,發(fā)現(xiàn)困惑,然后不斷進(jìn)步;《孟子》:中“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這些內(nèi)容都反映著我國(guó)人民的優(yōu)秀品質(zhì),通過(guò)教學(xué)能夠讓學(xué)生體悟中國(guó)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
教師不能一成不變地沿襲傳統(tǒng)的教學(xué)方法,而應(yīng)運(yùn)用多樣化的先進(jìn)教學(xué)手段,如運(yùn)用現(xiàn)代化的多媒體教學(xué)手段,用圖片、視頻再現(xiàn)古代歷史、詩(shī)詞畫(huà)面,引導(dǎo)和激發(fā)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讓學(xué)生準(zhǔn)確、生動(dòng)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識(shí)。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通過(guò)QQ群培養(yǎng)學(xué)生的自學(xué)意識(shí),通過(guò)提供自學(xué)參考書(shū)和網(wǎng)站的方式,讓學(xué)生有目的、有針對(duì)性地自主學(xué)習(xí),變被動(dòng)為主動(dòng),真正通過(guò)古漢語(yǔ)的教學(xué)完成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
參考文獻(xiàn):
[1][清]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王力.古代漢語(yǔ)[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9.
[3]湯可敬.說(shuō)文解字今釋[M].長(zhǎng)沙:岳麓書(shū)社,2002.
[4]徐復(fù),宋文民.說(shuō)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5]張淑琴.談高師古代漢語(yǔ)教學(xué)的文化傳承作用[J].寧波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01).
篇2
一、舊文獻(xiàn)新利用,對(duì)前人在一些文獻(xiàn)材料上的不當(dāng)看法進(jìn)行大膽糾正
譬如在對(duì)詩(shī)言志觀念產(chǎn)生時(shí)代這一論題的探討上,對(duì)于《今文尚書(shū)虞書(shū)舜典》里的詩(shī)言志的記載: 詩(shī)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有不少學(xué)者都認(rèn)為《堯典》、《舜典》皆系后世偽托,產(chǎn)生的時(shí)代較晚,因而詩(shī)言志觀念的產(chǎn)生時(shí)代也應(yīng)是較晚的。針對(duì)這一看法,筆者認(rèn)為: 詩(shī)言志這一觀念出現(xiàn)的早晚,與《堯典》《舜典》的寫(xiě)作時(shí)間乃是兩個(gè)不同的問(wèn)題,我們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即使《堯典》《舜典》真為西漢人所作,詩(shī)言志這一觀念也應(yīng)早就存在,只不過(guò)直到《堯典》《舜典》成書(shū)時(shí),才得以詩(shī)言志這一規(guī)范表述明確記載下來(lái)罷了。說(shuō)詩(shī)言志這段文字定形于戰(zhàn)國(guó)或戰(zhàn)國(guó)以后則可,說(shuō)詩(shī)言志這一詩(shī)學(xué)觀念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guó)或戰(zhàn)國(guó)以后就不恰當(dāng)了。十分明顯,經(jīng)過(guò)這一辨析,那種根據(jù)《堯典》《舜典》的產(chǎn)生時(shí)間來(lái)確定詩(shī)言志觀念的產(chǎn)生時(shí)間的做法自然也就無(wú)從立足了。
再譬如在對(duì)興觀群怨究系何指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對(duì)于《周禮春官大司樂(lè)》以樂(lè)語(yǔ)教國(guó)子興道諷誦言語(yǔ)這句話,有很多學(xué)者都喜把它讀為: 以樂(lè)語(yǔ)教國(guó)子: 興、道、諷、誦、言、語(yǔ)。這樣,就把興道諷誦言語(yǔ)看作了六種不同的表達(dá)方式。然而在筆者看來(lái)這句話的真正句讀應(yīng)該是: 以樂(lè)語(yǔ)教國(guó)子興道: 諷誦、言語(yǔ)。再具體說(shuō),也就是所謂樂(lè)語(yǔ)即配樂(lè)的歌詞,也即詩(shī)。興即興托,也即托詩(shī)言志。道即道說(shuō)、談?wù)摗R詷?lè)語(yǔ)教國(guó)子興道,其意即以樂(lè)曲所配之詩(shī)教授國(guó)子,使他們學(xué)會(huì)以托詩(shī)言志的方式進(jìn)行交際。諷誦即斷章賦詩(shī)。言語(yǔ)即論述引詩(shī),也即托詩(shī)而言、托詩(shī)而語(yǔ)。二者在表現(xiàn)形式上雖有不同,但是不管是言語(yǔ)引詩(shī)還是斷章賦詩(shī),兩者都是托詩(shī)而道,在這一點(diǎn)上二者則又是完全相通的。正因如此,所以《周禮》的作者才將興道一分為二,劃分為諷誦言語(yǔ)兩種形式。十分明顯,作這樣的解釋,不僅可以避免前人將興道諷誦言語(yǔ)一分為六的煩瑣和無(wú)據(jù),而且也與孔子的興觀群怨聯(lián)系了起來(lái),使我們由此對(duì)孔子的興觀群怨理論的具體含蘊(yùn)又獲得了一個(gè)更深切的認(rèn)識(shí)。
再譬如在對(duì)孔子是否有刪詩(shī)之舉這一論題的探討中,面對(duì)《論語(yǔ)》中也出現(xiàn)有逸詩(shī)的現(xiàn)象,有不少學(xué)者都認(rèn)為如果《詩(shī)經(jīng)》由孔子刪定,《論語(yǔ)》之中就不會(huì)出現(xiàn)逸詩(shī)。對(duì)此,筆者認(rèn)為《論語(yǔ)》之中雖有逸詩(shī),但是只有1 首,并且從這首逸詩(shī)所在的原文看: 棠棣之花,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yuǎn)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yuǎn)之有。孔子對(duì)這首詩(shī)完全持的是批判態(tài)度。這不僅不能說(shuō)明孔子未曾刪詩(shī),而且還恰恰證明由于孔子對(duì)這首詩(shī)所表述的觀點(diǎn)有異議,于是遂把它刪除了。十分明顯,以《論語(yǔ)》之中出現(xiàn)了1 首孔子所否定的逸詩(shī)為據(jù),就從而認(rèn)定孔子未曾刪詩(shī),這樣的論證邏輯也顯然太片面了。
再譬如在對(duì)兩漢文人的屈原情結(jié)及其心路歷程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對(duì)于西漢后期至東漢前期這一階段在揚(yáng)雄、班固等士人身上所出現(xiàn)的達(dá)則兼濟(jì),窮則獨(dú)善的明哲保身心理,有不少學(xué)者都持否定態(tài)度,認(rèn)為這是知識(shí)分子受儒家忠君、中庸思想的影響而導(dǎo)致的怯于反抗、懦弱茍且的卑微人格的表現(xiàn)。而筆者認(rèn)為這種達(dá)則兼濟(jì),窮則獨(dú)善的明哲保身心理,乃是在西漢后期至東漢前期這一階段儒學(xué)真正獲得獨(dú)尊的歷史條件下,知識(shí)分子的獨(dú)立意志因?yàn)槭苋寮易鹬刂R(shí)、尊重經(jīng)典的思想指向的鼓舞而導(dǎo)致的對(duì)于自我角色、自我地位重新反思的結(jié)果。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也就是這乃是知識(shí)分子人格覺(jué)醒,重視自我,敢于與最高統(tǒng)治者分庭抗禮的精神風(fēng)貌的體現(xiàn),將其視為兩漢知識(shí)分子人格理想處于低谷的反映,這顯然也是很不明智的。
二、積極發(fā)掘新的材料,對(duì)一些前人所忽視或重視不夠的材料進(jìn)行大膽采用
舉例來(lái)說(shuō),如在對(duì)詩(shī)言志的本義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對(duì)于《說(shuō)文》有關(guān)志字從心之聲的字形分析,盡管有不少學(xué)者也已看出這乃是從心從之之亦聲的簡(jiǎn)略說(shuō)法,志的本義乃是心有所之,心有所往,可是卻皆未能循此思路深入下去。而筆者則認(rèn)為我們應(yīng)當(dāng)抓住志字另外還有記憶記載之意的特點(diǎn),進(jìn)而分析: 所謂心有所之心有所往也就是心有牽掛、念念不忘的意思。因?yàn)樾挠袪繏臁⒛钅畈煌栽偌右瓴庞杏洃浻涊d的意思。這樣,通過(guò)對(duì)志的字形結(jié)構(gòu)與其具有記憶記載之意兩者之間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分析,就把志的念念不忘,情感強(qiáng)烈的突出特征凸出來(lái)了。毫無(wú)疑義,如果不是情感強(qiáng)烈,念念不忘,從志的本義是無(wú)論如何也不會(huì)引申出記憶記載的含義的。老子《道德經(jīng)》第55 章、33 章說(shuō): 心使氣曰強(qiáng),強(qiáng)行者有志,與此也同樣是可以相互佐證的。
再譬如在對(duì)賦比興的本義這一論題的探討中,由于劉勰對(duì)比的理論闡說(shuō)很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理應(yīng)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他所列舉的大量例子上。可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學(xué)界對(duì)于劉勰比興觀的研究,卻很少有學(xué)者對(duì)他所舉文例一一核對(duì)過(guò)。筆者通過(guò)對(duì)劉勰所舉之例的原始出處的一一檢索,發(fā)現(xiàn)他所舉的例子幾乎全部都是帶有比喻詞的,或者為如,或者為似,或者為若。舉例來(lái)說(shuō),如《詩(shī)經(jīng)大雅蕩》咨爾殷商,如蜩如螗,《衛(wèi)風(fēng)淇奧》有匪( 彼) 君子,如金如錫,《曹風(fēng)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鄭風(fēng)大叔于田》大叔于田,兩驂如舞,宋玉《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枚乘《菟園賦》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日等等。兩相比較,這與唐人孔穎達(dá)所說(shuō)的諸言如者皆比辭也顯然是高度一致的。如此,通過(guò)對(duì)劉、孔二家在對(duì)比的理解上的高度一致性的確認(rèn),我們對(duì)何為比興的認(rèn)識(shí)自然也就更為深入了。
再譬如在對(duì)先秦兩漢的辭體特征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對(duì)于《周易系辭傳上》的這一說(shuō)法: 書(shū)不盡言,圣人系辭焉以盡其言,兩千多年來(lái)對(duì)它有所接觸乃至有所研究的學(xué)者可謂不計(jì)其數(shù),可是卻從未有哪位學(xué)者注意到書(shū)辭言三者作為三種不同的表意形式,它們之間究竟有何區(qū)別。筆者認(rèn)為我們應(yīng)該根據(jù)這一表述自身的邏輯,大膽提出辭在上古乃指一種既不同于書(shū),也不同于言,但又能把言的豐富蘊(yùn)含充分表達(dá)出來(lái)的特殊語(yǔ)體。如果確定了這一認(rèn)識(shí),這無(wú)疑為我們有關(guān)辭在上古的特殊含義的探索打下了一個(gè)良好的基礎(ch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如果我們將這一表述與《周易》卦爻辭、春秋行人辭令、戰(zhàn)國(guó)縱橫之辭和屈宋楚辭結(jié)合起來(lái),我們對(duì)辭在上古的語(yǔ)體特征、文體特征的探索,是一定會(huì)產(chǎn)生一個(gè)嶄新的看法的。
再譬如在對(duì)孔子是否有刪詩(shī)之舉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學(xué)者們一般都會(huì)用到《左傳》襄二十九年有關(guān)季札觀樂(lè)的文獻(xiàn)記載: 吳公子札來(lái)聘,請(qǐng)觀于周樂(lè)為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xì)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 美哉,泱泱乎! 大風(fēng)也哉!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國(guó)未可量也。為之歌《陳》,曰:國(guó)無(wú)主,其能久乎?自《鄶( 檜) 》以下無(wú)譏焉。對(duì)于這則材料中季札對(duì)于《鄭風(fēng)》《陳風(fēng)》的貶評(píng): 其細(xì)已甚,民弗堪也,國(guó)無(wú)主,其能久乎,應(yīng)當(dāng)說(shuō)無(wú)論是孔子刪詩(shī)的肯定論者還是否定論者都應(yīng)看到了,可是千百年來(lái)也同樣未有哪位學(xué)者把它與孔子是否刪詩(shī)聯(lián)系起來(lái)。筆者認(rèn)為從《論語(yǔ)》中孔子的相關(guān)言論看,如非禮勿聽(tīng),非禮勿言、子不語(yǔ)怪力亂神、《詩(shī)》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wú)邪等,《詩(shī)》三百在孔子看來(lái)必定是無(wú)一不善的。可是眾所周知,季札觀樂(lè)時(shí)孔子已8歲。孔子8 歲時(shí),當(dāng)時(shí)的詩(shī)歌文本還良莠不齊,而在孔子成年后,《詩(shī)》三百卻已儼然變成篇篇合禮、語(yǔ)語(yǔ)無(wú)邪的經(jīng)典了,這其中的差別我們究竟應(yīng)怎樣看呢? 毫無(wú)疑問(wèn),如果否定孔子刪詩(shī),對(duì)這一現(xiàn)象我們也同樣是難以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的。
再譬如在對(duì)《孔雀東南飛》的思想主題這一論題的探討中,對(duì)于《毛詩(shī)序》的下面這段話,應(yīng)當(dāng)說(shuō)五四之后絕大多數(shù)研究《孔雀東南飛》的學(xué)者也都應(yīng)看到了: 詩(shī)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shī)故正得失,動(dòng)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shī)。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fēng)俗。可是遺憾的是在解釋《孔雀東南飛》的主題時(shí),學(xué)者們卻也同樣把這則材料忽略了。否則,所謂反封建反禮教反家長(zhǎng)制反包辦婚姻戀兒情結(jié)抱孫情結(jié),乃至更年期綜合征等等解釋也就不會(huì)出現(xiàn)了。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孔雀東南飛》主題的重新確立,當(dāng)然靠的并不是這一則材料,但是毋庸置疑,這則材料對(duì)于《孔雀東南飛》主題的重獲確立,無(wú)疑也是有舉足輕重的價(jià)值的。
三、注重相關(guān)概念原始關(guān)聯(lián)的探索,力避潛心枝葉,不顧本源
在先秦兩漢文學(xué)研究中,有一個(gè)現(xiàn)象十分突出,那就是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對(duì)個(gè)別概念、個(gè)別稱謂具體含義的探索,而對(duì)相關(guān)概念、相關(guān)稱謂之間的本源聯(lián)系則缺乏重視。這也是導(dǎo)致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傳統(tǒng)論題研究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舉例來(lái)說(shuō),如興字,它在先秦兩漢文學(xué)中就至少有兩種用法,一是賦比興之興,二是興觀群怨之興。對(duì)于這兩種用法的解釋,可以說(shuō)長(zhǎng)期以來(lái)學(xué)者們也都是分別進(jìn)行的。講賦比興的時(shí)候只講賦比興,講興觀群怨的時(shí)候只講興觀群怨,很少有談到二者的統(tǒng)一性的。而筆者認(rèn)為興字古文原作四手抬物之狀,它的本義就是托起、托舉的意思。無(wú)論是興觀群怨之興,還是賦比興之興,它們的含蘊(yùn)都與此有密切的聯(lián)系。再具體說(shuō),也就是無(wú)論是興觀群怨之興,還是賦比興之興,二者都是指對(duì)他者的依托。興觀群怨之興是指依托于《詩(shī)》,托《詩(shī)》而論; 賦比興之興是指依托于物,托物興起。前者反映了上古先民對(duì)經(jīng)典的取法,后者反映了上古先民對(duì)自然的仿效。十分明顯,通過(guò)對(duì)二者統(tǒng)一性的挖掘,我們不僅可以使它們彼此互證,而且也使它們各自的含義變得更為明確了。
再譬如辭字,在先秦兩漢文學(xué)里也有多重用法。如《周易》卦爻辭之辭,行人辭令縱橫之辭之辭,楚辭辭賦之辭,以及辭達(dá)而已修辭立誠(chéng)不以文害辭之辭等。對(duì)于辭的這些不同用法之間的聯(lián)系,前代學(xué)者雖也有所探索,但是他們的探索也同樣都是很不充分的。筆者認(rèn)為辭的用法雖然很多,但是它們都建基于這樣一個(gè)前提,即辭在上古乃是一種特殊的語(yǔ)體,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曲托假借、長(zhǎng)于文飾。如果我們能緊緊把握這一點(diǎn),那么無(wú)論對(duì)于辭的何種用法的認(rèn)識(shí),無(wú)疑都會(huì)由此變得更加通暢、更加透徹。比如孔子說(shuō)辭達(dá)而已,前人一般都把它理解為: 言辭,就是為了要把人的思想明確表達(dá)出來(lái)啊! 這樣認(rèn)識(shí)大而言之固然也不算錯(cuò),但是總讓人感到有失籠統(tǒng)。現(xiàn)在弄明了辭在上古的特殊含義,再來(lái)看孔子這句話就顯豁多了。原來(lái)孔子雖然認(rèn)為言之無(wú)文,行而不遠(yuǎn),但是對(duì)于辭的過(guò)分修飾、刻意雕琢,他也同樣是持反對(duì)態(tài)度的。
再譬如賦字,在先秦兩漢文學(xué)中它的用法也同樣有很多。如賦比興之賦,斷章賦詩(shī)之賦,古詩(shī)之賦,以及辭賦之賦等。對(duì)于賦的這些不同用法背后的聯(lián)系,前人的論釋也同樣很薄弱。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賦的各種用法的探索,也應(yīng)緊緊扣住它的本義。賦的本義雖為賦斂,但是上古賦斂之制卻有一個(gè)十分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只斂其本土所生,而不假外求。如果能把握賦的不假于外的特征,那么也就同樣可以把賦的各種不同用法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打通了。再明確說(shuō),也即是賦比興之賦指不假于物,也即不假比興,斷章賦詩(shī)之賦指不假音樂(lè),古詩(shī)之賦指可以配樂(lè),但沒(méi)有配樂(lè)的詩(shī),辭賦之賦指篇幅太長(zhǎng),無(wú)法配樂(lè)的詩(shī),或者介于散文與詩(shī)之間的一種無(wú)法詠唱的新的文體。如此,各種用法都與賦的本義相聯(lián)系,我們對(duì)賦的認(rèn)識(shí)自然也就變得更為全面了。
再譬如前人在解釋《離騷》之中的女?huà)€中正與求女時(shí),對(duì)于它們?nèi)叩暮x也往往是各自為釋的。由于未能將三者有機(jī)地聯(lián)系起來(lái),這就使我們?cè)谧x《離騷》的后半部分時(shí)總是感到頗多疑惑。鑒于此,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離騷》這三者的解釋,應(yīng)該將它們?nèi)挤旁凇峨x騷》一詩(shī)以男女喻君臣的大背景下來(lái)認(rèn)識(shí)。首先,根據(jù)楚人以姊為媭的舊俗,以及女?huà)€對(duì)于屈原不無(wú)關(guān)愛(ài)的詈語(yǔ),筆者認(rèn)為我們應(yīng)將女?huà)€定位為一位年事較高、涉世較深、做事圓滑,而又良心未泯,對(duì)屈原不乏關(guān)切之意的楚國(guó)老臣。而中正則是指屈原在受到女?huà)€不無(wú)善意的規(guī)諷責(zé)罵后,通過(guò)向重華陳辭,而從重華那里得到的求女自助的建議。由于屈原對(duì)大舜十分崇敬,因此對(duì)大舜的建議才以中正稱之。而所謂求女則應(yīng)如王逸所說(shuō),乃是求賢臣,即通過(guò)尋求其他賢臣的理解、幫助而改變自己在政治上孤立無(wú)援的危局。很顯然,由于把三者都放在了《離騷》以男女喻君臣的背景下,使它們得以互為貫通,互為映襯,這就使我們不僅加深了對(duì)三者的理解,而且也使整個(gè)《離騷》的后半部分因?yàn)槿叩谋舜撕魬?yīng)而變得更加意暢詞順。
四、對(duì)人的社會(huì)實(shí)踐,特別是言語(yǔ)活動(dòng)的復(fù)雜性給予高度重視,力避機(jī)械武斷,簡(jiǎn)單從事
眾所周知,人類(lèi)不僅是理性動(dòng)物,也是一種感性動(dòng)物,因此可以說(shuō)人的所有社會(huì)活動(dòng)都不可能是嚴(yán)格按照客觀的理性、科學(xué)的邏輯進(jìn)行的,語(yǔ)言活動(dòng)更是如此。因此在理解與先秦兩漢文學(xué)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材料時(shí),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這些歷史文獻(xiàn)所承載信息的復(fù)雜性也必須予以特別的關(guān)注,力避前人研究的不周延性。舉例來(lái)說(shuō),如對(duì)興的認(rèn)識(shí),有不少學(xué)者都喜把賦比興之興理解為觸景生情,這顯然是帶有望文生義之嫌的。因?yàn)橛|景生情固然是先寫(xiě)外物,然后再說(shuō)人事,但師法自然、假托于物也同樣是先寫(xiě)外物,然后再說(shuō)人事。先物后人的表述形式與觸景生情顯然并不是一對(duì)一的關(guān)系。在這種情況下僅憑直覺(jué)就武斷地認(rèn)為這種先物后人的語(yǔ)言形式就是觸景生情的體現(xiàn),這樣的結(jié)論顯然太草率了。
再譬如對(duì)于賦的探討,有不少學(xué)者都認(rèn)為漢大賦的曲終奏雅乃是志在諷諫,或者也可能是作家內(nèi)心矛盾的反映。志在諷諫或作家內(nèi)心有矛盾,固然都可呈現(xiàn)為曲終奏雅的形態(tài),但騁才宣情,炫示藻采,追求淋漓盡致、登峰造極的超越性宣泄也同樣可以以曲終奏雅為掩護(hù),為自己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有效的外衣。表象雖只一個(gè),但形成這種表象的原因卻很多,面對(duì)這種情況我們顯然也是不能輕下結(jié)論的。
篇3
依據(jù)人文素質(zhì)教育理念,在原有課程體系基礎(chǔ)上修改和完善,無(wú)需另建一套課程體系,而是使新增設(shè)的人文素質(zhì)教育課程與原有的課程相互照應(yīng),融于同一個(gè)大的課程體系中,形成一個(gè)有機(jī)的課程整體,使課程結(jié)構(gòu)更合理、更科學(xué)。具體如下:一是在通識(shí)課程中增設(shè)最基本的人文素質(zhì)教育必修課程,如人文素質(zhì)教育通論、現(xiàn)代社交禮儀、美學(xué)與美育、中國(guó)通史、古典名著導(dǎo)讀與鑒賞、實(shí)用書(shū)法書(shū)寫(xiě)與欣賞、世界名曲欣賞等,并給予相應(yīng)的學(xué)分。二是結(jié)合學(xué)科課程滲透人文素質(zhì)教育。如古代文學(xué)教師可以結(jié)合專業(yè)必修課、專業(yè)選修課、公共選修課等在教學(xué)中對(duì)文學(xué)院以及全學(xué)院學(xué)生進(jìn)行人文素質(zhì)教育。三是根據(jù)專業(yè)特點(diǎn)開(kāi)設(shè)與其相對(duì)應(yīng)的人文素質(zhì)教育課程。可以在專業(yè)必修課中增設(shè)相應(yīng)的專業(yè)人文素質(zhì)教育課程,并給予相應(yīng)的學(xué)分,如開(kāi)設(shè)哲學(xué)史、戲劇史、教育史等。
二、調(diào)整教學(xué)內(nèi)容
這是強(qiáng)化大學(xué)生素質(zhì)教育與培養(yǎng)的關(guān)鍵。文學(xué)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披露的是華夏民族的精氣神、炎黃子孫的奮斗史、華夏江山的正氣歌,其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財(cái)富。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要彰顯人文素質(zhì)的精華。既要固守文化傳承,使古代文學(xué)的精華得以繼承和發(fā)揚(yáng),培養(yǎng)深厚的人文底蘊(yùn),還要強(qiáng)化古代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意識(shí),古代文人提出眾多創(chuàng)新思想:“守舊無(wú)功”“質(zhì)疑問(wèn)難”“濯去舊見(jiàn)以來(lái)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學(xué)中的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意識(shí),成為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價(jià)值取向,古代文學(xué)把創(chuàng)新作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養(yǎng)目標(biāo),使學(xué)生樹(shù)立創(chuàng)新意識(shí),與時(shí)俱進(jìn)。更要關(guān)注情商教育,培養(yǎng)現(xiàn)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發(fā)展健康個(gè)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為學(xué)生面對(duì)社會(huì)壓力、人生挫折的動(dòng)力源泉。
三、建設(shè)師資隊(duì)伍
教師是學(xué)生人文素質(zhì)教育的主導(dǎo),師者深厚的人文素質(zhì)儲(chǔ)備,是教師隊(duì)伍建設(shè)的關(guān)鍵。師者應(yīng)具有廣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融文學(xué)、史學(xué)、哲學(xué)、藝術(shù)、審美、天文、地理等各領(lǐng)域?yàn)橐粻t,以敏銳深邃的時(shí)代感受,形成對(duì)生命、對(duì)生活、對(duì)社會(huì)的獨(dú)特體悟。教師的人文素養(yǎng),便是教之內(nèi)功、師之根本。師資隊(duì)伍建設(shè),要注意師資來(lái)源,應(yīng)盡量從本校現(xiàn)有的授課教師中挑選,個(gè)別的可外聘;師資培訓(xùn),可采取校內(nèi)、校外兩種方式。從事必修課和專業(yè)課講授的教師可參加校外舉辦的高級(jí)培訓(xùn)班或培訓(xùn)中心的學(xué)習(xí)。一般的授課教師要參加校內(nèi)普通培訓(xùn)班的學(xué)習(xí),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導(dǎo)思想、基本內(nèi)容、基本方法等知識(shí),提高全體教師的人文素養(yǎng)和教育水平。
四、營(yíng)造文化氛圍
重視社會(huì)實(shí)踐環(huán)節(jié),拓展人文素質(zhì)教育的培養(yǎng)空間。校園環(huán)境的文化氛圍,對(duì)學(xué)生人文素質(zhì)教育與培養(yǎng)具有強(qiáng)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開(kāi)展多元文化活動(dòng),使學(xué)生的人格得到塑造,個(gè)性得到發(fā)展,精神得到升華。如請(qǐng)專家學(xué)者作系列人文講座或?qū)W術(shù)報(bào)告,引導(dǎo)學(xué)生提高人文素養(yǎng);以校報(bào)、校園網(wǎng)和廣播站為載體,開(kāi)設(shè)人文教育專欄,拓展校園文化活動(dòng)空間;建立人文社團(tuán),如新聞、文學(xué)、楹聯(lián)、藝術(shù)等協(xié)會(huì)或社團(tuán);開(kāi)展健康向上、格調(diào)高雅、內(nèi)容豐富的校園文化生活,包括開(kāi)展古典名著讀書(shū)報(bào)告會(huì)、經(jīng)典誦讀和演講比賽等活動(dòng)。老師還應(yīng)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空間來(lái)營(yíng)造濃厚的人文氛圍,使學(xué)生從中學(xué)習(xí)知識(shí)、開(kāi)闊視野、美化心靈、娛樂(lè)身心,是培養(yǎng)學(xué)生人文底蘊(yùn)、塑造學(xué)生人文情懷的有效途徑。
五、結(jié)語(yǔ)
篇4
論文關(guān)鍵詞: 古代文學(xué) 人文精神 教學(xué)
論文摘 要: 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過(guò)程對(duì)其進(jìn)行有意識(shí)的發(fā)掘與弘揚(yáng),有益于陶冶學(xué)生性情與塑造其價(jià)值信仰。在具體教學(xué)實(shí)踐中教師需要以文本為中心,使學(xué)生打好學(xué)識(shí)基礎(chǔ),引入性情領(lǐng)會(huì),進(jìn)而貫通歷史蘊(yùn)含與當(dāng)下情懷,由此解讀出古代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的人文價(jià)值。
就面向過(guò)去的古代文學(xué)而言,其教與學(xué)的過(guò)程就是對(duì)歷史維度的文學(xué)作品、文學(xué)作家、文學(xué)現(xiàn)象,以及內(nèi)在規(guī)律進(jìn)行全方位的探索與認(rèn)知。而在這一歷程中所面臨的文本對(duì)象及其承載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可以說(shuō)是一種歷史傳承下來(lái)的深湛智慧精華。對(duì)于后來(lái)者來(lái)說(shuō),它不僅僅是一種知識(shí),更可以在其中尋找一個(gè)精神的棲居之地,進(jìn)行個(gè)人心靈、道德、價(jià)值觀、人生觀的洗禮與重塑。而這也就是悠久傳統(tǒng)孕育的古代文學(xué)的人文精神的價(jià)值體現(xiàn)之一。
但是,即使一個(gè)蘊(yùn)含豐富的礦藏也需要開(kāi)采者得其礦脈而入才能真正發(fā)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學(xué)人文精神教學(xué)傳遞的路途上,如何進(jìn)行是需要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慎重思慮和實(shí)施的。面對(duì)古代文學(xué)文本,教學(xué)的環(huán)境與一般的讀者閱讀有所不同,它不僅僅是個(gè)人化的閱讀與隨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種公共的語(yǔ)言環(huán)境中對(duì)文本進(jìn)行品讀、分析,其所面臨的不單是一個(gè)個(gè)體對(duì)于文本的闡釋問(wèn)題,還需要在課堂的對(duì)話條件下對(duì)古代文學(xué)的人文精神進(jìn)行適度和妥帖的傳達(dá),才能使其對(duì)學(xué)生主體自身的思想與情感產(chǎn)生一定的輻射影響,從而發(fā)揮出古代文學(xué)所蘊(yùn)含的人文精神的價(jià)值。
一、以文為本
人文教育,因?yàn)槠鋵?duì)于學(xué)生主體的道德完善與人格成長(zhǎng)的重要意義而備受青睞。而對(duì)“人”的完善與培養(yǎng),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標(biāo)。但是所謂“人”的塑造實(shí)現(xiàn)不是理論的空談,它是要在具體的教學(xué)中憑依著“文本”所開(kāi)拓生發(fā)的環(huán)境而衍生的。在教師、學(xué)生、文本三者構(gòu)成的教學(xué)環(huán)境中,無(wú)論是作為導(dǎo)引者的教師,還是作為接受者的學(xué)生,他們二者對(duì)于人文精神的傳達(dá)與領(lǐng)悟都離不開(kāi)以“文”為本的立場(chǎng)。
在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進(jìn)程中要解讀歷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懷與藝術(shù)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觸作品,浸入文本思路,與文本共同思想進(jìn)而體會(huì)領(lǐng)悟。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教學(xué)活動(dòng)便是圍繞著一定的文本,以一種師生對(duì)于文本的解讀與闡釋貫穿始終。所謂“論從史出”,一切的闡釋都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應(yīng)以文本語(yǔ)義為基礎(chǔ),以忠實(shí)于文本原意為基本原則。而古代文學(xué)作品作為一種經(jīng)典文本,它對(duì)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其與當(dāng)下語(yǔ)言與文化存在一定時(shí)空落差,尤其所呈現(xiàn)的語(yǔ)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時(shí)候會(huì)成為學(xué)生理解文本語(yǔ)義的一重障礙。
就作為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最古老的一部詩(shī)集——《詩(shī)經(jīng)》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義障礙,真正地解讀似乎是很難繼續(xù)深入的。就《詩(shī)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而言,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學(xué)生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會(huì)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語(yǔ)義與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學(xué)習(xí)思維,文字的障礙就凸顯出來(lái)。文字的困難性會(huì)讓學(xué)生產(chǎn)生一定的挫折感,這在許多時(shí)候顯然成為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進(jìn)程中的一個(gè)問(wèn)題。而更關(guān)鍵的是,在作品閱讀中,如果文字意義的辯定與解析不明就會(huì)使得接下來(lái)文意疏通、詩(shī)意理解和精神升華等一系列的教學(xué)導(dǎo)向發(fā)生偏差與誤讀。譬如《詩(shī)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第二章有“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一句,從前句可辯,文意說(shuō)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傷悲與擔(dān)心憂懼又作何解呢?朱東潤(rùn)《中國(guó)歷代文學(xué)作品》中注釋曰:“采桑女心里傷悲,害怕被公子們擄去。”顯然這里是把“公子”理解為一種富貴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義。而學(xué)生往往會(huì)從自己習(xí)慣語(yǔ)言意識(shí)中判定:“公子”專指男性,再與“擄”字聯(lián)系往往在腦海中解讀成了一種強(qiáng)搶民女的意味。這時(shí)就需要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進(jìn)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為公子嫁為媵,故治蠶以備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時(shí)忽然悲傷,以其將及公子同歸也。”[1]而“歸”字之意也不是“回歸”而是“女子出嫁”。由此,進(jìn)一步引申出“古代貴族嫁女必以侄娣從之”的媵婚制習(xí)俗。而在此語(yǔ)義與文化的背景上,再發(fā)掘“女心傷悲”的情感蘊(yùn)含就會(huì)從直接的“社會(huì)沖突意義”進(jìn)而向女子“恐遠(yuǎn)父母兄弟”,以及“傷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繼續(xù)發(fā)掘。
上述所言的教學(xué)過(guò)程與思路作為一個(gè)例證突出的是對(duì)文本的解釋與依賴,也許從某種程度上有些趨于傳統(tǒng)的知識(shí)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張僵硬的知識(shí)灌輸,而是著意表明一種“打好基礎(chǔ)”的教學(xué)立場(chǎng)。畢竟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文本相對(duì)于其他文本來(lái)說(shuō)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殊性,而無(wú)論從教師還是學(xué)生的角度講,文本識(shí)別與語(yǔ)義辨析不是教學(xué)的終點(diǎn)站,而是我們搭建的必要的腳下的橋梁,有了它的溝通,教與學(xué)才能自然實(shí)現(xiàn)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學(xué)始終都是人的文學(xué),歷代的經(jīng)典作品中往往蘊(yùn)含著深厚的人生情感與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過(guò)文學(xué)作品接觸與領(lǐng)悟凝結(jié)于其中的個(gè)人與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對(duì)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與人文素養(yǎng),是有著顯而易見(jiàn)的效應(yīng)的。而要達(dá)成這個(gè)目標(biāo)效果,顯然僅僅依靠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中對(duì)作品文本的語(yǔ)義和文獻(xiàn)的考證講析和概念傳達(dá)是不夠的,真摯地深入文學(xué)作品解讀其人文情感,還需在文學(xué)課堂上引入性情來(lái)體驗(yàn)與主導(dǎo)。這也就意味著,教師不僅要掌握傳統(tǒng)的方法解讀文本,將學(xué)生帶入古典語(yǔ)境,而且應(yīng)在教學(xué)中“發(fā)揚(yáng)真美,以?shī)嗜饲椤保琜2]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guò)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學(xué)的生命力。
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作品往往具有鮮明的意象、深遠(yuǎn)的意境與不羈的想象,對(duì)于它的解讀,理性的拆解與分析有時(shí)候往往會(huì)有損其情境的渾融和圓滿,直接的結(jié)論宣導(dǎo)也無(wú)益于對(duì)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讀方式有時(shí)會(huì)對(duì)作品情志的傳達(dá)起到一種直接的作用。 轉(zhuǎn)貼于 所謂性情化的作品解讀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傾向于領(lǐng)悟式的體驗(yàn)閱讀與理解,它重在實(shí)踐一種獲得結(jié)論的過(guò)程,從而使學(xué)生在富有情感的環(huán)境感召下,激發(fā)自身對(duì)作品情感體驗(yàn)的認(rèn)同。引入性情主導(dǎo)的文本教學(xué),有時(shí)可以通過(guò)對(duì)經(jīng)典原著文本的熟讀,先獲得文本語(yǔ)感,然后在反復(fù)吟詠體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領(lǐng)會(huì)情境,積累情感,從而深入到對(duì)文本的深層體會(huì)中。當(dāng)然這首先要建立在語(yǔ)義暢通、文化熟悉的基礎(chǔ)之上。以《詩(shī)經(jīng)·周南·芣苡》為例,這是一首古老的歌謠。文學(xué)史中多稱其是“一首描寫(xiě)婦女們采摘芣苡的勞動(dòng)之歌,全詩(shī)洋溢著歡愉之情”。但是這一主題概要顯然需要具體的閱讀體會(huì)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對(duì)這首十分簡(jiǎn)短的作品,許多理性分析與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幫助學(xué)生理解其審美之妙境。譬如從《詩(shī)序》說(shuō)“婦人樂(lè)有子矣”出發(fā)考量“芣苡”的“治愈不孕”藥用之途,由此來(lái)發(fā)掘先民對(duì)生殖的崇拜和狂熱的詩(shī)歌主題。這顯然是一條深入發(fā)掘詩(shī)歌內(nèi)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卻似乎忽略了詩(shī)中蘊(yùn)含的情感與情緒的直接傳達(dá)。《芣苡》全詩(shī)十二句,只換了六個(gè)動(dòng)詞,形成了一種輕快的節(jié)奏,此時(shí)富有情感的誦讀可以說(shuō)是體會(huì)詩(shī)歌歡樂(lè)情緒的一種直接方式。而要體會(huì)整體的詩(shī)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讀與知識(shí)消化之后,以一種真實(shí)的心靈和想象來(lái)領(lǐng)悟《芣苡》的完整情境:“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shī),恍聽(tīng)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fēng)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yuǎn)若近,忽斷忽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3]這種心曠神怡的陶冶,也是涵養(yǎng)性情與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學(xué)中性情引入的主張,可以說(shuō)是一種基于以“情”體“情”的思維,它雖然傾向于體悟性情感閱讀,但卻是應(yīng)以一定的知識(shí)作為基礎(chǔ)的。它追求的應(yīng)是一種有知有情的既樸實(shí)又富有性靈的教學(xué)過(guò)程。
三、當(dāng)下重塑
古代作品蘊(yùn)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學(xué)中充分發(fā)揮效力,則需要跨越歷史與當(dāng)下的距離來(lái)形成最終的共鳴,從而能夠走進(jìn)當(dāng)下,進(jìn)入學(xué)生人格成長(zhǎng)與培養(yǎng)的發(fā)展歷程,彰顯古代文學(xué)人文蘊(yùn)含之于現(xiàn)實(shí)與人生的價(jià)值。
一般普遍認(rèn)為,作品的意義和精神可以從很多層次上來(lái)理解,即作品創(chuàng)作時(shí)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傳中的闡釋與當(dāng)下對(duì)文本意義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中,顯然需要面對(duì)這重重意義解讀。首先必須考慮的是作品醞釀與誕生時(shí)的本意,它雖不一定是解讀作品的唯一準(zhǔn)則,但確是不能忽視的生成起點(diǎn)。而在其完成之后于歷史變遷中不同文化視野下的解讀,作為曾經(jīng)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與作品共生傳播了。那么處于當(dāng)下環(huán)境的教學(xué),明顯在時(shí)間與文化空間上與其所面對(duì)的文本存在距離,于是作為詮釋者的教師則需要溝通“彼”與“此”,將歷史語(yǔ)境中的文本移于當(dāng)下文化語(yǔ)境中,讓學(xué)生形成與文本的溝通。
于是,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課堂中便似乎面臨著兩個(gè)方向的發(fā)掘與引導(dǎo)。既要引領(lǐng)學(xué)生走入過(guò)去,重新體驗(yàn)文學(xué)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來(lái)立足當(dāng)下,讓學(xué)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傳達(dá)的人文意義境界。畢竟“解釋傳統(tǒng)的根本要義就在于指向現(xiàn)在,射向當(dāng)前”。[4]而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對(duì)于人文精神的發(fā)掘的意義也恰在于這種傳統(tǒng)生命精神對(duì)現(xiàn)代生存的啟迪。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以當(dāng)下意識(shí)闡釋經(jīng)典文本新的價(jià)值內(nèi)涵與精神意義時(shí),可以說(shuō)既是對(duì)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傳承。但是含蓄蘊(yùn)藉的古代文學(xué)本身,以及歷代文論的繁復(fù)和時(shí)代的遠(yuǎn)離,使得當(dāng)下教學(xué)環(huán)境中對(duì)古代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與精神的理解趨于復(fù)雜。那些文學(xué)之作中既有一種于歷史流變中凝固的價(jià)值核心,又具有隨文化環(huán)境不停變化的豐富的意義和當(dāng)下的多重闡釋可能。于是在教學(xué)這個(gè)公共語(yǔ)言環(huán)境中,面對(duì)著當(dāng)下多元的闡釋與趨向過(guò)度的解釋,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新的精神價(jià)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進(jìn)當(dāng)下進(jìn)程、體現(xiàn)當(dāng)下關(guān)懷的同時(shí),還需在慎重選擇中以一種適度性的立場(chǎng)來(lái)貫通古今。
參考文獻(xiàn):
[1]姚際恒.詩(shī)經(jīng)通論[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58.
[2]魯迅.魯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篇5
論文摘 要: 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過(guò)程對(duì)其進(jìn)行有意識(shí)的發(fā)掘與弘揚(yáng),有益于陶冶學(xué)生性情與塑造其價(jià)值信仰。在具體教學(xué)實(shí)踐中教師需要以文本為中心,使學(xué)生打好學(xué)識(shí)基礎(chǔ),引入性情領(lǐng)會(huì),進(jìn)而貫通歷史蘊(yùn)含與當(dāng)下情懷,由此解讀出古代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的人文價(jià)值。
就面向過(guò)去的古代文學(xué)而言,其教與學(xué)的過(guò)程就是對(duì)歷史維度的文學(xué)作品、文學(xué)作家、文學(xué)現(xiàn)象,以及內(nèi)在規(guī)律進(jìn)行全方位的探索與認(rèn)知。而在這一歷程中所面臨的文本對(duì)象及其承載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可以說(shuō)是一種歷史傳承下來(lái)的深湛智慧精華。對(duì)于后來(lái)者來(lái)說(shuō),它不僅僅是一種知識(shí),更可以在其中尋找一個(gè)精神的棲居之地,進(jìn)行個(gè)人心靈、道德、價(jià)值觀、人生觀的洗禮與重塑。而這也就是悠久傳統(tǒng)孕育的古代文學(xué)的人文精神的價(jià)值體現(xiàn)之一。
但是,即使一個(gè)蘊(yùn)含豐富的礦藏也需要開(kāi)采者得其礦脈而入才能真正發(fā)掘到其中的精髓,所以在古代文學(xué)人文精神教學(xué)傳遞的路途上,如何進(jìn)行是需要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慎重思慮和實(shí)施的。面對(duì)古代文學(xué)文本,教學(xué)的環(huán)境與一般的讀者閱讀有所不同,它不僅僅是個(gè)人化的閱讀與隨想式的感悟,更要在一種公共的語(yǔ)言環(huán)境中對(duì)文本進(jìn)行品讀、分析,其所面臨的不單是一個(gè)個(gè)體對(duì)于文本的闡釋問(wèn)題,還需要在課堂的對(duì)話條件下對(duì)古代文學(xué)的人文精神進(jìn)行適度和妥帖的傳達(dá),才能使其對(duì)學(xué)生主體自身的思想與情感產(chǎn)生一定的輻射影響,從而發(fā)揮出古代文學(xué)所蘊(yùn)含的人文精神的價(jià)值。
一、以文為本
人文教育,因?yàn)槠鋵?duì)于學(xué)生主體的道德完善與人格成長(zhǎng)的重要意義而備受青睞。而對(duì)“人”的完善與培養(yǎng),一直是其所追崇的目標(biāo)。但是所謂“人”的塑造實(shí)現(xiàn)不是理論的空談,它是要在具體的教學(xué)中憑依著“文本”所開(kāi)拓生發(fā)的環(huán)境而衍生的。在教師、學(xué)生、文本三者構(gòu)成的教學(xué)環(huán)境中,無(wú)論是作為導(dǎo)引者的教師,還是作為接受者的學(xué)生,他們二者對(duì)于人文精神的傳達(dá)與領(lǐng)悟都離不開(kāi)以“文”為本的立場(chǎng)。
在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進(jìn)程中要解讀歷代作家的信念理想、人文情懷與藝術(shù)精神,就需要直接地接觸作品,浸入文本思路,與文本共同思想進(jìn)而體會(huì)領(lǐng)悟。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教學(xué)活動(dòng)便是圍繞著一定的文本,以一種師生對(duì)于文本的解讀與闡釋貫穿始終。所謂“論從史出”,一切的闡釋都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應(yīng)以文本語(yǔ)義為基礎(chǔ),以忠實(shí)于文本原意為基本原則。而古代文學(xué)作品作為一種經(jīng)典文本,它對(duì)學(xué)生來(lái)說(shuō),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其與當(dāng)下語(yǔ)言與文化存在一定時(shí)空落差,尤其所呈現(xiàn)的語(yǔ)言文字的古老性,有時(shí)候會(huì)成為學(xué)生理解文本語(yǔ)義的一重障礙。
就作為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最古老的一部詩(shī)集——《詩(shī)經(jīng)》而言,如果不首先跨越文字的意義障礙,真正地解讀似乎是很難繼續(xù)深入的。就《詩(shī)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而言,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學(xué)生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會(huì)首先被古老的文字語(yǔ)義與陌生的文化背景阻隔了深入的學(xué)習(xí)思維,文字的障礙就凸顯出來(lái)。文字的困難性會(huì)讓學(xué)生產(chǎn)生一定的挫折感,這在許多時(shí)候顯然成為了學(xué)生學(xué)習(xí)進(jìn)程中的一個(gè)問(wèn)題。而更關(guān)鍵的是,在作品閱讀中,如果文字意義的辯定與解析不明就會(huì)使得接下來(lái)文意疏通、詩(shī)意理解和精神升華等一系列的教學(xué)導(dǎo)向發(fā)生偏差與誤讀。譬如《詩(shī)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第二章有“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一句,從前句可辯,文意說(shuō)的是春季女子采桑之事,但是暖暖的春日中,女子之傷悲與擔(dān)心憂懼又作何解呢?朱東潤(rùn)《中國(guó)歷代文學(xué)作品》中注釋曰:“采桑女心里傷悲,害怕被公子們擄去。”顯然這里是把“公子”理解為一種富貴人家的子弟的普遍意義。而學(xué)生往往會(huì)從自己習(xí)慣語(yǔ)言意識(shí)中判定:“公子”專指男性,再與“擄”字聯(lián)系往往在腦海中解讀成了一種強(qiáng)搶民女的意味。這時(shí)就需要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結(jié)合相關(guān)文獻(xiàn)進(jìn)行深入的文字辨析:“公子,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宮,將隨為公子嫁為媵,故治蠶以備衣裳之用,而于采桑時(shí)忽然悲傷,以其將及公子同歸也。”[1]而“歸”字之意也不是“回歸”而是“女子出嫁”。由此,進(jìn)一步引申出“古代貴族嫁女必以侄娣從之”的媵婚制習(xí)俗。而在此語(yǔ)義與文化的背景上,再發(fā)掘“女心傷悲”的情感蘊(yùn)含就會(huì)從直接的“社會(huì)沖突意義”進(jìn)而向女子“恐遠(yuǎn)父母兄弟”,以及“傷春悲己”的情感角度繼續(xù)發(fā)掘。
上述所言的教學(xué)過(guò)程與思路作為一個(gè)例證突出的是對(duì)文本的解釋與依賴,也許從某種程度上有些趨于傳統(tǒng)的知識(shí)性的辨析,但是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主張僵硬的知識(shí)灌輸,而是著意表明一種“打好基礎(chǔ)”的教學(xué)立場(chǎng)。畢竟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文本相對(duì)于其他文本來(lái)說(shuō)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殊性,而無(wú)論從教師還是學(xué)生的角度講,文本識(shí)別與語(yǔ)義辨析不是教學(xué)的終點(diǎn)站,而是我們搭建的必要的腳下的橋梁,有了它的溝通,教與學(xué)才能自然實(shí)現(xiàn)理解的目的。
二、引入性情
文學(xué)始終都是人的文學(xué),歷代的經(jīng)典作品中往往蘊(yùn)含著深厚的人生情感與深刻的生命感悟。而通過(guò)文學(xué)作品接觸與領(lǐng)悟凝結(jié)于其中的個(gè)人與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對(duì)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與人文素養(yǎng),是有著顯而易見(jiàn)的效應(yīng)的。而要達(dá)成這個(gè)目標(biāo)效果,顯然僅僅依靠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中對(duì)作品文本的語(yǔ)義和文獻(xiàn)的考證講析和概念傳達(dá)是不夠的,真摯地深入文學(xué)作品解讀其人文情感,還需在文學(xué)課堂上引入性情來(lái)體驗(yàn)與主導(dǎo)。這也就意味著,教師不僅要掌握傳統(tǒng)的方法解讀文本,將學(xué)生帶入古典語(yǔ)境,而且應(yīng)在教學(xué)中“發(fā)揚(yáng)真美,以?shī)嗜饲椤?[2]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guò)可感的形象,自然地感受文學(xué)的生命力。
經(jīng)典的文學(xué)作品往往具有鮮明的意象、深遠(yuǎn)的意境與不羈的想象,對(duì)于它的解讀,理性的拆解與分析有時(shí)候往往會(huì)有損其情境的渾融和圓滿,直接的結(jié)論宣導(dǎo)也無(wú)益于對(duì)作品真正的理解。而性情化的解讀方式有時(shí)會(huì)對(duì)作品情志的傳達(dá)起到一種直接的作用。
所謂性情化的作品解讀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傾向于領(lǐng)悟式的體驗(yàn)閱讀與理解,它重在實(shí)踐一種獲得結(jié)論的過(guò)程,從而使學(xué)生在富有情感的環(huán)境感召下,激發(fā)自身對(duì)作品情感體驗(yàn)的認(rèn)同。引入性情主導(dǎo)的文本教學(xué),有時(shí)可以通過(guò)對(duì)經(jīng)典原著文本的熟讀,先獲得文本語(yǔ)感,然后在反復(fù)吟詠體味中,感知古文意象,領(lǐng)會(huì)情境,積累情感,從而深入到對(duì)文本的深層體會(huì)中。當(dāng)然這首先要建立在語(yǔ)義暢通、文化熟悉的基礎(chǔ)之上。以《詩(shī)經(jīng)·周南·芣苡》為例,這是一首古老的歌謠。文學(xué)史中多稱其是“一首描寫(xiě)婦女們采摘芣苡的勞動(dòng)之歌,全詩(shī)洋溢著歡愉之情”。但是這一主題概要顯然需要具體的閱讀體會(huì)才能真正被消化。而對(duì)這首十分簡(jiǎn)短的作品,許多理性分析與探究似乎并不利于幫助學(xué)生理解其審美之妙境。譬如從《詩(shī)序》說(shuō)“婦人樂(lè)有子矣”出發(fā)考量“芣苡”的“治愈不孕”藥用之途,由此來(lái)發(fā)掘先民對(duì)生殖的崇拜和狂熱的詩(shī)歌主題。這顯然是一條深入發(fā)掘詩(shī)歌內(nèi)涵的有益思路,但是卻似乎忽略了詩(shī)中蘊(yùn)含的情感與情緒的直接傳達(dá)。《芣苡》全詩(shī)十二句,只換了六個(gè)動(dòng)詞,形成了一種輕快的節(jié)奏,此時(shí)富有情感的誦讀可以說(shuō)是體會(huì)詩(shī)歌歡樂(lè)情緒的一種直接方式。而要體會(huì)整體的詩(shī)境,也不妨在理性解讀與知識(shí)消化之后,以一種真實(shí)的心靈和想象來(lái)領(lǐng)悟《芣苡》的完整情境:“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shī),恍聽(tīng)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fēng)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yuǎn)若近,忽斷忽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3]這種心曠神怡的陶冶,也是涵養(yǎng)性情與品格的重要方式。
教學(xué)中性情引入的主張,可以說(shuō)是一種基于以“情”體“情”的思維,它雖然傾向于體悟性情感閱讀,但卻是應(yīng)以一定的知識(shí)作為基礎(chǔ)的。它追求的應(yīng)是一種有知有情的既樸實(shí)又富有性靈的教學(xué)過(guò)程。
三、當(dāng)下重塑
古代作品蘊(yùn)含深厚的人文精神,但其要在教學(xué)中充分發(fā)揮效力,則需要跨越歷史與當(dāng)下的距離來(lái)形成最終的共鳴,從而能夠走進(jìn)當(dāng)下,進(jìn)入學(xué)生人格成長(zhǎng)與培養(yǎng)的發(fā)展歷程,彰顯古代文學(xué)人文蘊(yùn)含之于現(xiàn)實(shí)與人生的價(jià)值。
一般普遍認(rèn)為,作品的意義和精神可以從很多層次上來(lái)理解,即作品創(chuàng)作時(shí)的原意、文本被作者完成之后流傳中的闡釋與當(dāng)下對(duì)文本意義生成的理解。那么在古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中,顯然需要面對(duì)這重重意義解讀。首先必須考慮的是作品醞釀與誕生時(shí)的本意,它雖不一定是解讀作品的唯一準(zhǔn)則,但確是不能忽視的生成起點(diǎn)。而在其完成之后于歷史變遷中不同文化視野下的解讀,作為曾經(jīng)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與作品共生傳播了。那么處于當(dāng)下環(huán)境的教學(xué),明顯在時(shí)間與文化空間上與其所面對(duì)的文本存在距離,于是作為詮釋者的教師則需要溝通“彼”與“此”,將歷史語(yǔ)境中的文本移于當(dāng)下文化語(yǔ)境中,讓學(xué)生形成與文本的溝通。
于是,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課堂中便似乎面臨著兩個(gè)方向的發(fā)掘與引導(dǎo)。既要引領(lǐng)學(xué)生走入過(guò)去,重新體驗(yàn)文學(xué)之作本身所指人文境界,又要走出來(lái)立足當(dāng)下,讓學(xué)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傳達(dá)的人文意義境界。畢竟“解釋傳統(tǒng)的根本要義就在于指向現(xiàn)在,射向當(dāng)前”。[4]而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對(duì)于人文精神的發(fā)掘的意義也恰在于這種傳統(tǒng)生命精神對(duì)現(xiàn)代生存的啟迪。在教學(xué)過(guò)程中以當(dāng)下意識(shí)闡釋經(jīng)典文本新的價(jià)值內(nèi)涵與精神意義時(shí),可以說(shuō)既是對(duì)于它的重塑又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傳承。但是含蓄蘊(yùn)藉的古代文學(xué)本身,以及歷代文論的繁復(fù)和時(shí)代的遠(yuǎn)離,使得當(dāng)下教學(xué)環(huán)境中對(duì)古代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與精神的理解趨于復(fù)雜。那些文學(xué)之作中既有一種于歷史流變中凝固的價(jià)值核心,又具有隨文化環(huán)境不停變化的豐富的意義和當(dāng)下的多重闡釋可能。于是在教學(xué)這個(gè)公共語(yǔ)言環(huán)境中,面對(duì)著當(dāng)下多元的闡釋與趨向過(guò)度的解釋,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新的精神價(jià)值的重塑在注重其走進(jìn)當(dāng)下進(jìn)程、體現(xiàn)當(dāng)下關(guān)懷的同時(shí),還需在慎重選擇中以一種適度性的立場(chǎng)來(lái)貫通古今。
參考文獻(xiàn):
[1]姚際恒.詩(shī)經(jīng)通論[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58.
[2]魯迅.魯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